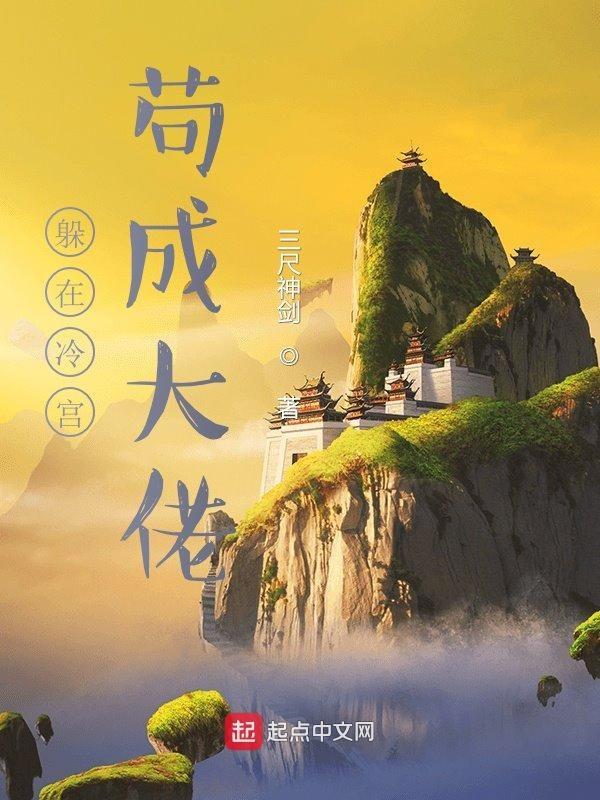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六州歌头txt > 300310(第32页)
300310(第32页)
贺今行说:“不论明悯愿意与否,都要先把这个机会给他。哪怕他因守孝而拒绝,这也是一种态度——朝廷需要他,丁忧回乡只是暂时。”
顾元铮再看他一眼,抱臂道:“小贺大人倒是个明白人。你们这个年纪的书生,我娘让我见过一些,大都酸得很。少有正经的,也带着几分天真。”
贺今行笑了笑,“若是有‘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也没什么不好,多历练就成。”
顾元铮莞然。
哪个读书人没几分大志向?但践行出来的可就少之有少。她不管人说什么,只看他们做成了什么。
穿出游廊,正厅檐下已挂上一排灯笼。兵丁们把几套桌凳搬到院中,烧的是大锅菜,一桌摆几大盘。
周碾过来拜见,贺今行与他说了几句话。顾横之则先入座,留出身边的位置。
顾元铮坐在对面,看他俩挨着坐说小话,敲了敲桌面,提高声气道:“明后日要不挑个空,一起去拜访忠义侯,把莲子接过来?”
两人便住了嘴一齐看向她。顾横之没有异议,说:“拜帖该递,但莲子未必愿意来。”
顾元铮道:“小孩子心性不全,与家人常年分别有许多委屈,因此口是心非,很正常。我们做兄姊的,岂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这话不止现在,我明日觐见也是这么说。”
顾横之微叹,“那就再试试。”
顾元铮看向他身边,“小贺大人怎么看?”
贺今行直觉陛下不会轻易被说动,如实道:“难。”
“再难也得想办法解决。”顾元铮叫下属拿来几个大碗一字摆开,亲自提坛子倒酒,给桌上每个人一碗。最后那碗放到了贺今行面前,“他兄弟俩总得回去一个,不然让我舅舅和舅母怎么办?小贺大人你说是不是?”
烈酒气息冲鼻,贺今行正要开口,旁侧伸来一臂端走那碗酒。
顾横之仰脖饮尽,翻转酒碗示给对座,“铮姐,你想怎么办,跟我说就好。”
“咱们晚些是得好好谈谈。”顾元铮露齿而笑,举起酒碗隔空跟他干一个。
顾横之拿空碗做了个样子,没有再沾酒。
“啧,出去才几年啊,酒量就变浅了。”顾元铮嘲笑自家弟弟,又对贺今行道:“小贺大人是聪明人,在下就不多嘴了。”
贺今行微微颔首,叠掌回了半礼。
顾横之提过酒坛给自己倒满一碗酒,盯着他大姐,“阿姐,顾钰敬你。”
姐弟多年,顾元铮清楚再说下去真要把人惹毛了,但她仍然说:“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很煞风景,我说这些也不是为你好,是为了我自己。但我必须要提醒你,有些事你没法回避,早晚要面对。如今多事之秋,快刀斩乱麻才是上策。”
她说完,等着顾横之反驳,青年却只与她干尽那碗酒。
顾元铮见此也有些感伤,独自喝酒,一言不发。
杨弘毅受不了饭桌上鸦雀无声,主动开口转移话题,再不谈前言,净说些南疆与西北的趣事,勉强也算宾主尽欢。
饭后小坐片刻,贺今行与诸人告辞。
顾横之很想请他留宿,但一直到他要走,都没能说出口。他不得不送他回去,提灯穿过前院门,他忽然说了声“抱歉”。
“嗯?”贺今行止住步伐,转身面对他。
月与灯相映,人与影交缠。
顾横之说:“莲子,我爹娘,关于他们的事,都应由我和家里解决,不该牵扯到你。”
贺今行先前便隐约猜到缘由,认真道:“我以为我们之间已有牵绊。所谓‘牵绊’,就是你我一体,命运相连,诸事共处。你既为难,我岂能旁观?莲子一直很思念家乡,每次蒙阴要来人,他接到信之后,就日日到永定门去。他总说是玩乐,但我知道他想走出那座城门,我也希望他能离开京城,回到你们的母亲身边去。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帮他实现愿望。”
顾横之:“他离家十三年,爹、娘与我都对他亏欠良多,想办法弥补他是我的责任。但你不一样,纵有儿时情谊,你依然不欠他什么。铮姐说的话,你也别放在心上。若是往常,我一定不吝请你帮忙。可眼下朝局多变多灾,我又听说你要推行新策,正如履春冰。如此紧要关头,我不想因为我,让你被束缚、被掣肘。”
通政司现在是风头正盛,但以陛下的性情,焉知哪日不会触及逆鳞,朝承恩暮赐死。越是炙手可热,越有焚身之险。
“这不是束缚。”贺今行向他伸出手,“君心难测,若是陛下怀疑我厌弃我,想寻由头治我,没有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事。那些与我政见相左、想要针对我的同僚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在朝为官身处局中,就免不了。但不管天上风晴雨雪,我们都得往前走,迈出步子才知道过不过得去。就算脚下的路不好走,我也还有你啊。”
掌心摊开在眼前,顾横之轻轻握住。他从来不是瞻前顾后的人,可遇到与今行有关的事,总忍不住多想许多。
要怎样,才能助你所行皆坦途?
月色朦胧,沉默好像忧愁。
贺今行便做主动的那个人,牵着对方向前走。相携到大门上,几只灯笼将里外照得亮堂堂,遂放开手,“你和铮姐还有事要谈,就送到这里,明天再见?”
顾横之不肯,依然驾车送他回去。
经行繁华夜市,一排排花灯架子竖立长街两侧,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