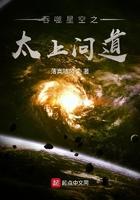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六州歌头txt > 210220(第9页)
210220(第9页)
仿若实质的目光把崔连壁看得脸颊抽了抽,感情是想让他去找姓顾的调和。但顾横之进京跟他没关系,他现在凑过去劝人大度,那脸皮得有多厚啊?
他不能接这摊子,于是张口就来:“这事儿下官没法办。顾穰生前年踩坏我灯笼我还记着呢,他这人就是蔫儿坏,让他儿子代他来,咱们和他协商还得传信。要传也行,但我跟他说话就是对牛弹琴,别说他听不懂,他就算听懂了也装不懂,没法沟通。”
“而且依下官看,人家这要求并不过分啊。南越交出罪魁祸首就能了结一切,推几个奴隶出来算什么?毫无诚意。您二位也不是不明白,得施压才行。”他按着长桌,边说边倾身过去,声音随之压低,“下官知道现在的国库打不起仗,但指不定,这些南越人就想试探咱们,是不是虚张声势呢?”
屋里安静下来,屋外三两同僚的闲聊骤然响了不少。
少钦,秦毓章摇铃唤了名舍人进来,“去叫傅大人来见我。”
裴孟檀看着那舍人领命快步离开,笑了一下,开口依旧是温和的:“秦相爷是有成算了。”
秦毓章整理着袍袖起身,只道:“不能再拖了。”
崔连壁侧身避让,转头邀裴相爷一道去用饭。
非他不愿同秦相爷为伍,只是秦相爷日日清粥小菜,不如裴大人的精食细脍有蹭头。
当天晚上,乔装打扮的南越使臣随两名扈从走进内城一座今年才开的酒楼,小心翼翼上了雅阁,见到大喇喇地坐在酒桌后头等他的傅禹成,才松了口气。坐下道:“傅大人,昨天不是约好去飞还楼的么?”
临时改地址,吓得他以为出什么事了。
傅大人面容扭曲了一瞬,啐道:“去你爹!”
唾沫喷头,那使臣也当即变了脸色,“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毁坏条约了吗?”
“我倒要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傅禹成一拍桌子,冷笑:“我吃喝玩乐样样顶级地供着你们,说好签订条约,结果你临到头反悔,一日拖一日。我在政事堂替你们顶着压力,丢尽脸面,你倒是吃喝得挺舒服啊?要这样下去,这条约不结了,你们滚回南越,等着顾氏的铁骑打进银蛇城罢!反正也不是没打进去过。”
使臣脸色又是一变,但明白他是来施压了,咬牙挨着他坐下,诉苦:“实不相瞒,那位领主是我们王上最要好的兄弟,王上怎么可能答应交出他呢?赔款好说,让我们王上为难,我回去后这人头可就不保了啊。”
他打了个手势,身后扈从将一只宝箱放到傅禹成面前,打开来,满箱金银珠宝浮光灿灿。
“还望傅大人再替鄙人说说情,转圜一二。”
后者颧骨下的皮肉跳了跳,手摸到宝箱上,却是拉上了箱盖,“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但再拖下去,我是真顶不住了。今日议事,秦相爷说了,此事年前无法了结,那就不谈了。”
他左右看看,示意随从都到外面去盯着,而后压声道:“兄弟又怎样,你们王上愿意拿他自己的命换兄弟的命不成?再者说了,你们随便找个人顶替,姓顾的和那些边军还能认出真假?”
不谈的意思,就是要武力解决。
傅禹成这个办法,未必不可行,就是屈辱了些。但与顾氏铁骑兵临王城相比,又不算什么。
“这……”使臣却陷入两难,并非为邦国,而是忧心自己的身家性命。王上的兄弟发起怒来,奈何不了宣朝,奈何得了他啊。
傅禹成看他这样子,心知事成了大半,也不着急,就摩挲着宝箱等待。
另一名扈从忽然上前来,出声问:“秦毓章真的这么说?”
南越的奴隶脸上尽皆烙印,有碍观瞻,是以入京时都包了头脸。这人也不例外,就是身材比寻常奴隶高大一些。
然而不论强弱都是奴隶,贸然插嘴直呼尊讳未免太不知分寸。
傅禹成正要呵斥,却见这人拆下头巾,露出一张粗糙却光洁的脸来。轮廓分明,五官深邃,是与南越人、宣人都不同的长相。
他到嘴边的斥责立刻变成了惊悚:“西……?”好在剩下两个字被他及时打住。
“傅大人何必如此惊讶?”这人好整以暇地在他对面坐下,“您往常收钱的时候可一点不手软啊。”
雅阁外的鼎沸人声如潮水消逝,凝重起来。
一夜过去,雪霁初晴。
宣京四千里外的云织县衙,贺今行背着行囊,在点卯之前便启程。
同一时刻,按照惯例今年需得回京述职的殷侯于仙慈关出发。他们路程一致,但不好同行。
三天之后的下午,贺今行先一步赶到遥陵。
持鸳早早准备,为他做好了合身的衣装。冬日穿得厚重,披风一裹,就看不出身形是否有女子的玲珑。贺冬留下的换声的药丸也还有整整一瓶。
第二日上午,一小支马队带着西北的风沙与烟尘跨过黍水,踏入古镇。
贺今行换上女装,戴上面纱,待声音柔和下来才去迎接。却发现不止他爹,贺长期也回来了。
“大帅。”他抱拳见过礼,轮到后者,迟疑地叫了一声“堂兄”。
盯着他爹的人不会少,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贺长期却没反应,好似神游天外。他又叫了一声,对方才慌忙回礼,之后随队进入别院,一直面色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