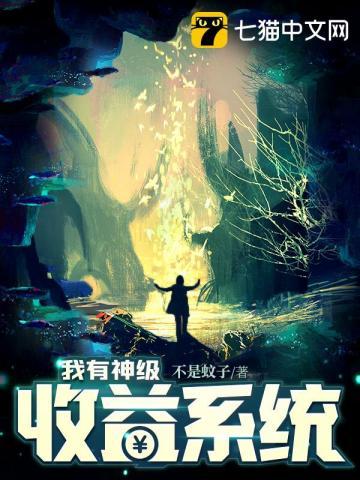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虫族渣攻谈恋爱呢 > 7080(第21页)
7080(第21页)
“兴许是想去遛弯了。”苻缭道,“上次才偷吃了苻延厚那儿的鲜草,不过他也不会发现就是了。”
苻药肃对这只白花花的羊还挺喜欢,特别是阿兰带着念儿来时,念儿一看见它就想摸,它也不攻击人,让苻药肃对它好感直直上升。
“那我带它去转转。”苻药肃笑道,“也是延厚不在……”
说到这儿,他提醒道:“以后还是不要和爹提起这些,他要是问了,你说辞了便好,他也不会再多追究,延厚又不认得官场上的人,他也没证据。”
苻缭应下,苻药肃便打开门,绵羊就在门前立着。苻药肃摸了摸它,它便跟着苻药肃走了。
见绵羊没有异样,苻缭才松了口气。
这时候,沙沙的脚步声又传来了。
苻缭提起的心一下子落空。
若是奚吝俭,不会惹出这么大的脚步声。
“小季。”苻缭走到缺口处,果然见到的是季怜渎,“你现在可以出宫了?”
“哪儿能呢。”季怜渎摆了摆手,“但宫内那么大,谁知道我跑哪里去,借口怎么都能找出来。”
他看起来没什么要紧事,比先前松弛不少,苻缭猜测,他在宫内应该是风生水起。
“你早时昏过去,被奚吝俭带走了。”季怜渎道,“我怕你出什么事,回来就好了。”
季怜渎一提起这个,苻缭便想起自己昏过去的缘由,脸上不由得一热。
季怜渎继续道:“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苻缭突然发觉自己身上的沉香气味很浓,浓到季怜渎也能闻出来。
“他哪会对我做什么?”苻缭笑得有些勉强,“这不,我一醒就回来了。”
话是这么应付过去,可苻缭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
他感觉,迟早有一天纸包不住火。
先前要离开的打算再次浮上心头。
苻缭在魂不守舍,季怜渎早已先入为主地认为苻缭是心里有鬼。
事实确实如此。
季怜渎可是清楚地知道他们俩有什么事,更别提苻缭晕倒时奚吝俭铁青的面色,还有他不由分说便要把人带走的时候,连御医都来不及叫,坐上轿子就带回他府上了。
也就是那时候人不多,再没人知道这事,否则就凭奚吝俭先前散下的那些与自己的流言,可是要被人抓着把柄的。
于是季怜渎故意笑道:“怎么啦,我只是问一下而已,怎么你反应这么大?难道是早就移情别恋了?我就说哪有感情是长久的呢?”
“没有!我怎么可能……”苻缭一下激动起来,又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是说、我没……”
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转而问道:“小季,你可是又遇到什么事了,才这样说?”
是自己昏迷期间,他们有了什么交流,让季怜渎误会更大了,还是季怜渎已经发觉自己的真实情意?
季怜渎见情况不对,连忙道:“阿缭,我开玩笑的,你别紧张。我一直觉得有愧于你,你若不把心思放在我身上,我反倒还松了口气呢。”
看苻缭脸都涨红了,嘴唇又是发白的,便知他实在是害怕。
季怜渎不免唏嘘。
这又是何必呢。
他都不明白苻缭怎么会看上奚吝俭。
奚吝俭估计满脑子怎么把官家从龙椅上弄下来,他那性格又不会随意让旁人插手,向他献媚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他都不为所动。
苻缭又不是什么重要的身份,奚吝俭又怎会花心思在他身上?
而且,奚吝俭竟然也对苻缭有些事儿。
就自己被关在璟王府那段时间,光听声音就知道奚吝俭忙于正事,与苻缭又哪有那么多碰面时间。
这两个人,莫名其妙。
不过,奚吝俭要是能因为苻缭而无心权斗,倒也挺好。
不然他总会坏自己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