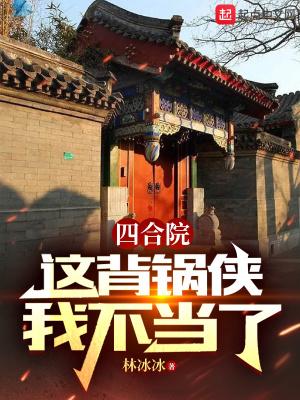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临时暧昧免费 > 100108(第16页)
100108(第16页)
酒半醒不醒的谢安青说:“你困不困?”
陈礼:“困。”
谢安青:“我们去个地方。”
陈礼:“翻墙去河岸?”
谢安青:“不是。”
陈礼:“那是?”
谢安青:“你先起来。”t?
陈礼太困了,起了一下没起来,跌回到纯棉花打的被褥里。
谢安青俯身去抱陈礼,结果因为酒没醒,力气不足,抱到一半的时候,两人一起摔了回去。
陈礼胸口被个大活人砸中,立马清醒,她把大半夜了还在闹幺蛾子的人摁在床上亲了半天,亲到她喉咙里的声音开始出现情谷欠时,起身穿衣服,穿鞋,之后把她也收拾妥当,问:“去哪儿?”
谢安青偏头看了没有窗的南面几秒,说:“院里,画墙,这次把你也画上去。”
陈礼心里被轻挠了一下。
今天回来的时候,她投在院墙的视线又被发现了,有人都喝醉了,还惦记着给她的心脏打下一个补丁。
她说:“还有国庆。”
陈礼冷脸,说:“这句我听不到。”
听到也不画。
两个人的世界多一条狗太挤了。
谢安青盯着陈礼不说话。
半天,陈礼说:“听到了,听到了。起来,再磨蹭天都亮了。”
陈礼话这么说,心里则想,反正笔在她手里,她不想画狗,谁还能把刀架她脖子上不成。
陈礼牵着谢安青下楼,一会儿找手电,一会儿找笔刷,前后折腾十多分钟才终于出来门外,陈礼刷子刚碰到墙,忽然被谢安青抢走。
“你手不好,”谢安青说,“我画。”
陈礼眉毛挑老高。
她都不知道谢安青还有这才艺。
藏得够深啊。
“行,你画,我给你打手电。”陈礼退到旁边,给谢安青当手电支架。
谢安青站在墙前不动,像是在规划,非常认真,一看就是……
“…………”
陈礼把手电筒夹在胳膊底下,在谢安青完成最后一笔,把刷子扔进捅里那秒,两手相对,“啪,啪,啪。”
谢安青回头:“我画得好不好看?”
陈礼:“简直完美。”
谢安青很矜持地抿住想要上扬的嘴角,说:“谢谢。”
然后跨出花圃往院里走。
陈礼又看了眼墙一眼,拿出手机连拍数十张,迅速弯腰提桶。
谢安青已经走到了鱼池边,声音淡淡地,说:“我画画这么好,奶奶为什么只让我学写字、吹笛,不让我学画画?”
陈礼快步走过来,把挡住谢安青去路的,一根细到蜜蜂站上去都要晃上两晃的树枝拨开,说:“奶奶怕你累到。”
谢安青点一点头,往前走一步,往后退一步,转身抱住陈礼说:“礼姐,困。”
陈礼只能扔下桶,先把人抱回房间。
再下来,陈礼犹豫了几秒,只关门提桶,没动谢安青的惊世大作。
第二天一早,谢槐夏的尖叫从前院一直传到二楼。谢安青闭着眼摇了摇宿醉之后钝痛的头,问:“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