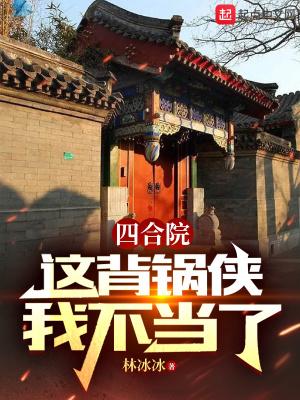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六州歌头by一别都门三改 > 240250(第21页)
240250(第21页)
陆续有人发现其他线索,一合计,确定这批人就是运送粮草的辎重队。
贺长期感到不妙:“这么多辎重,粮草武器都有,恐怕要发生大战。”
敌后消息不通,然而他们从观测到的西凉人各部队调动的情况,也能推测一二。这些狗贼平静了一两个月,忽然大规模地调遣辎重,必然是为了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
第一次撞见辎重队是十天前,前线很可能已经开战。
“咱们去把这一队劫了?”有人提议。
他们在敌后几个月,风餐露宿,还能保持人样,全靠劫杀西凉人。
若是能烧毁敌军粮草,或是截断运输,以缓解己方前线压力,当然最好不过。但是,贺长期环视一圈,存活到现在的人手实在太少了,甚至比不上西凉人押运队伍的零头。
“先跟上,到时候再觑机行事。”
一队人便草草挖了些野菜下肚,顺着车辙开拔——也只有这种负担大、行程慢的辎重队,他们才能靠两条腿跑步追踪。
一路时远时近,到太阳落山,西凉军再次扎营过夜。押运骑兵大约一千人,十分谨慎,结了圆阵,将辎重队伍围在中间,又设了几层岗哨铺出一里。
待他们炊饭过后,大部分进了营帐,贺长期才匍匐着接近,试图先摸清对方岗哨明暗、轮换频次。
月夜下的草原十分活跃,他遇到不少小动物,忍了又忍,才没抓住它们拿回去打牙祭。直到前伸的手背上忽然落下湿热的触感,他一如既往准备挥开,然后在下一刻反应过来,这他娘的是人手!
两只手迅速互抓手臂,把对方拉向自己,再顺着臂肩探向脖颈。两人眨眼间就在草丛里滚成一团,拳脚互搏几轮,草折虫散,却听不见一丝人声。
“小贺将军?”对方忽然出声,“别打了,是我。”
“你谁?”
“牧野镰啊!”
一炷香后,贺长期和牧野镰各带着自己的人,在几里外的山包背后碰面。
“小贺将军,你们收拾得可真干净。”后者见面就发出惊叹。反观自己手下,除了举人师爷,尽是衣衫褴褛,形容脏污,跟乞丐似的。
贺长期不动声色地将这百十来人扫视了一遍,只道:“我任职百总,担不得‘将军’两个字。”
“我看好你,现在不是将军,以后肯定是。我先叫着,你也不吃亏嘛。”牧野镰过来揽他,跟他哥俩好似的说:“英雄不提来处。我就问一句,你们是不是也想打劫那一队西凉兵?那可是大肥羊啊,咱们都吃不下,不如合作,一起薅他几把羊毛。”
贺长期皱眉:“我记得你是被羁押在狱的匪徒。”
“嗨,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牧野镰嘻嘻笑,也把他们这几个兵看来看去,“我是匪徒不错,但是小贺将军,我人多,还有马哦。”
他的师爷正经说:“马不太好,老瘦的多,所以我们想从那些西凉人手里抢一些马匹过来。”
“嗯,我看过,他们拉车的马就是大遂滩的马。”牧野镰点点头。他想要的东西,不管过多久,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得到。
“赶马可不容易。”贺长期养过马,也送过马。
牧野镰很自信:“这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贺长期想到对方能驭狼,想必有些不为人知的本事。此情此景也顾不得谁是逃犯,一切都以对抗西凉人为先,他便开诚布公:“我们不需要马,我们是要烧他们的粮草。”
“噫,玩儿这么大?”牧野镰惊讶了一瞬,双眼却渐渐放出光芒,就像夜里的狼,兴奋道:“好啊!那我不止要把我的马抢回来,还要烧他们的粮草,烧得越多越好,叫他们没得饭吃,也尝尝饿得想啃人的滋味儿!”
双方约定了合作,当即便重新侦查,而后回来商议行动计划。
贺长期进行总结:“你们去赶马,吸引押运队的注意力,能把他们引出营地更好。我们趁机去烧粮草,只要大火能起,他们必定回来救火,你们也就能顺利逃脱。”
“那你们烧了粮草之后怎么脱身?”
“当然是趁乱跑啊。”
牧野镰满意点头,“嗯,不要变成飞蛾扑进火里就好,不然我来捞你也会引火烧身,很难办的。”
贺长期没理他,领着自己人做了些简易的伪装,潜行绕到西凉人营地的后方。
已入子夜,一朵浓云遮了月亮。
“老天也助我们。”贺长期无声说,蛰伏许久,忽听营地前方爆发骚乱。
牧野镰那边按照计划开始行动。
贺长期则保持着匍匐的姿势,直到后方的西凉骑兵去了前方,只剩下少量的岗哨,才示意大家前进。
众人依次动身,配合默契,呼吸间便能放倒一个岗哨,然后把人的甲胄头盔扒下来穿到自己身上。
这是他们几个月来做了不知多少回的事,熟练得很,这回只是要解决的人多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