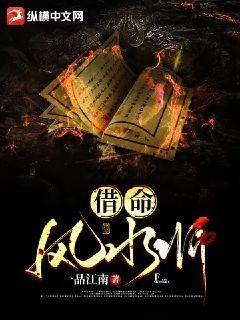秃鹫小说>她不是潘金莲书评 > 5060(第10页)
5060(第10页)
时修笑道:“这不是正在查嚜。”
林掌柜满脸困惑,见进来客人,又忙着招呼去了。
“大人,要不要张贴告示缉拿那五个贼人?我已命那两个巡夜的到衙里画像去了。”臧班头满面振奋,“只要抓着他们,案子就算破了!少不得一定是这几个人趁夜潜入姜家行窃,给那姜俞生撞见,于是他们便杀人灭口。”
时修只缓缓点点头,“既是贼,自然是要拿的,下晌就叫人把告示贴出去。”
西屏看他有些漫不经心,因问:“怎么,你觉得那几个贼匪不是杀害大爷的真凶?”
时修囫囵吃了个馄饨,烫得直咧嘴,呜哇哇说的什么叫人听不懂。她马上垮下脸皱起鼻子,嫌弃地睇住他,“你就不能咽下去再说话么!”
“我是说,要是五个贼匪杀的姜俞生,犯得着把书房里那张地毯弄得那样?那地毯一看就是因剧烈挣扎蹬揣得皱起来好几处,五个大男人,竟弄不住姜俞生一个?”
西屏早上只在门外头看,倒未留意。
臧志和却是看清楚了的,只是粗心忘了,这时经时修一提,脸色立时变得悻悻然,“大人说得是,那姜俞生虽然人高马大,可还不至于五个汉子还制他不住。既如此,那几个人贼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难道是巧合?可那间书房里分明丢了东西,这又怎么说?”
时修一时也想不明白,只得先吃饭,“吃过饭后,你遣人回衙去,叫那仵作再把姜俞生的尸首细细验一遍。”
此刻他不由得想起南台的好处,朝西屏挑着眉峰笑了下,“要是姜南台在,兴许还能验出什么别的东西。今日那仵作老眼昏花的,我看他未必验得明白。”
西屏撇了下嘴,“三叔这会都不知道走多远了。”
时修默了片刻,忽想到什么,脸色一变,郑重其事地搁下箸儿吩咐臧志和,“你派人去路上把那姜南台追回来。”
西屏骤然语塞,不知他什么一会变张脸,到底什么用意,是为案子还是赌气?
这厢吃过饭进去,路上问起来,他不说缘故,反问起她来:“你还记不记得,先前我们怀疑,是你那三叔将我们已查明的姜丽华死因的消息透露给了姜俞生。我在想,如果我们怀疑得真,那他为什么要透露给他?”
西屏手上捏着朵月季花,一下一下地往地上掷地着花瓣,“你不是说他是有心要提醒大爷,叫有所防备嚜。”
他转过脸来,眼睛朝天上斜去,喉间含混地滚了一句过去,“我当时那是怄气的话。”
她不知真没听清还是假没听清,仰着面孔笑,“你说什么?”
他当时是含着酸意,所以才说南台是有意透露的消息,眼下想来也没道理,姜南台要是成心,早就该说了。不过要他承认是吃醋污蔑,简直有损英明。他才不认!便一拂袖,不大耐烦地往前走了。
第54章是外贼?
西屏小步跑上去,隔会憋不住笑出了声。时修听了益发气恼,转头瞪她一眼,“你笑什么?!”
她把嘴一歪,“我笑不论多英明的人,原来吃起醋来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就把罪名往人头上扣。”
噎得他无话可说。她说得不错,无论多英明决断的人,也有情关难过。他悲哀地在心里叹气,反剪起手来,故意恶狠狠地瞪她一眼,“我还要给姜南台扣个更大的罪名呢,没准行凶杀人的就是他!”
“这话怎么说?”
“你想想看,如果他不是有意想要姜俞生知道消息后防范,那走漏消息的事,就是他的无心之失。却是怎么个无心法?”
西屏思忖片刻,迷糊地摇头,“你说呢?”
“我说?”他懒得说,可又不得不说,因为这推测关乎着姜俞生的死因,“要我说,也许他是气不过,私下去找姜俞生替你打抱不平,争执中说漏了嘴。所以姜俞生才连夜打发了相关证人,串通着周大人把他也急忙调去宝应县,否则他不会走得那样急。”
这倒极有可能,否则早不早晚不晚的,南台没道理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向姜俞生。西屏思虑间,不觉掐断了花梗,随手丢在一旁,疾步走上去,“没了?”
时修瞥她一眼,“为你,他对姜俞生怀恨在前,又与姜俞生争执在后,这难道还不够成为杀人的动机?”
西屏当他还是在吃醋,骄傲地歪着脸,“照你这么说,我还是那个罪魁祸首囖?”
那叶间射下来的光斑在她面颊上晃荡,他看她一会,渐渐敛了笑容,转过身朝前走了。
过一会,又把手剪到背后来,朝她勾一勾。
西屏咯咯笑着跑上去,四下无人,只见翠色逼匝中,遍地金齑,周遭的花草林木就是天然的屏障,隔绝了所有的眼睛,她放心地把手放在他背后的手里。
时修一握住她的手,就改了口,“或许是我多疑,姜南台没有空暇作案,姜俞生死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歇在城外的驿馆里了。”
西屏点头道:“照你这思路,其实四姨娘最有嫌疑,连我也有嫌疑了。”
时修有些听不得这话,把眉一皱,“还是先顺着谋财害命这条线索查吧,那屋里现成丢了东西,总不能明摆着的不先去问,只做这些无凭无证的推断。”
西屏想来也是这道理,跟着点头。
从那一截树荫中走出来,她收回了手,脸上带着赧红,自己把手交握在前头,“那些贼是怎么进来的呢?我们那角门常日都是从里头拴着的,大门一更后也关上了。”
“贼要进来还不容易?翻墙就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