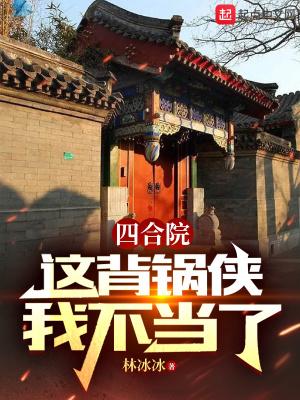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皇太女是什么意思 > 第六章(第3页)
第六章(第3页)
皇帝眉心微蹙,似是有些厌倦。
景昭看着父亲的脸色,毫不怀疑他下一秒会脱口而出说一句真烦,抢先皱眉道:“在饮食里下毒、收买皇城禁卫、安排刺客……都是些老套的戏码,还有吗?”
还有吗?
这三个字从皇太女口中轻飘飘说出,就像是敲打在云华郡主心头的一记丧钟。
她原本很是愤恨,很是不甘,很想冷笑。然而随着这三个字落入耳中,她的心忽然一颤又一颤,像是有一只大手拧住了心脏,心底生出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
另一个声音从她的身后传来,夹杂在殿外连绵的雨声里,语调平稳中带着无尽的哀意:“没有了。”
刹那间有如九天雷霆当头劈下,直直劈落在云华郡主的天灵盖上。
她眼前阵阵发黑,耳畔剧烈嗡鸣,艰难挣扎着试图回头,丝毫不顾双臂和腰膝扭曲拉扯出剧烈疼痛。
在她身旁,礼王世子的嚎哭声戛然而止。这对暗怀隔阂的兄妹此刻心有灵犀,同时竭力挣扎着回望,瞳孔倒映出一个异常熟悉的身影。
素衣的礼王妃踏进殿内。
她的脚步停在一双儿女身前,定定看着狼狈不堪的儿女,眼底痛楚难掩,紧接着拜倒在地:“妾身养子不教,难辞其咎,前来请罪。”
“起来吧。”景昭温和道,“王妃识大体、明大局,是有功之人,无需自责。”
礼王妃叩首三下,才依言起身。
礼王世子颤声:“母亲?你这是……你出卖了我们?”
云华郡主嘶声道:“母亲!你糊涂啊!”
听着身后儿女的嘶喊责怪,礼王妃一寸一寸僵硬地转过头,看着儿女愤怒扭曲的神情,眼底泪水涌起,咬牙冷声道:“所以呢?你们想让我怎么做?”
她看向礼王世子:“你从小由你父亲亲自教养,我插不了手,让他将你养成这幅眼大心空的模样,偏偏又没脑子,太后挑唆几句,就真的敢大胆图谋。我这做娘的,你从来看不起,只觉得我不如你父亲英明,不如你祖母宠爱你,只是个没什么见识的后宅妇人……你要自寻死路,我拦不住你。”
在礼王世子的叫骂声中,礼王妃又转向云华郡主,看着女儿眼底的怒意,木然片刻,泪水终于滴落下来。
“还有你。”礼王妃哀声道,“云华,你总觉得不公平,觉得你父亲和祖母偏爱景煜——可是你何曾看得起娘?在你眼里,你父亲和太后的图谋是宏图大志,娘则瞻前顾后难成大事,是么?”
“可是凭什么啊?”礼王妃终于哭出声来,“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是我在你心里,不也是‘泼出去的水’?我嫁进景家,就该听你们景家人的话,不考虑自己的娘家。你们要图谋大事,何曾把我的意见听在耳中,把我的态度看在心里。这等抄家灭族的大罪,你们儿戏一般,什么都不过脑子,太后怂恿几句,我这双好儿女,一个盲听盲从,一个不管不顾,真就敢提着脑袋上。”
“那我的娘家怎么办?建元五年我们王家因为你们父亲的愚蠢举动,险些遭了祸事,建元十年再来一次吗?”
礼王妃拭泪道:“抄家灭门的大罪,行事如同儿戏,不听从我的劝告,却要我陪着你们玩命,还要赔上王家满门?从夫从子,也不是这个从法;忠孝礼义,忠在最前面。你们要怨我恨我,我这个做娘的都认了,可我不心虚。”
礼王妃含泪陈辞掷地有声,一时间就连景昭都没有说话。
正在此时,床榻上忽然传来剧烈的嗬嗬声,太后喉头猛烈颤动,双眼圆睁有若厉鬼,所有人立刻定睛看去,只听太后勉强挤出一口气,怒斥道:“小贱妇!”
听到太后声音的那一刹,礼王妃猛地抬首。
她对着自己的儿女时,尚在垂泪哀叹,然而当她听见太后的声音时,牙关紧咬柳眉倒竖,显然恨到了极点,提起裙摆疾步走进屏风后面,见皇帝与太女面色毫无波动,先拜了一拜,旋即扑向太后床前。
饶是郑嬷嬷身体健壮忠心耿耿,都没挡住看似娇弱的礼王妃,反被重重搡开跌坐在地。
礼王妃扑至床前,一把攥住了太后领口,眼底恨意有若实质。
“老虔婆!”她厉声喝道,“你害我儿女,这帐怎么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