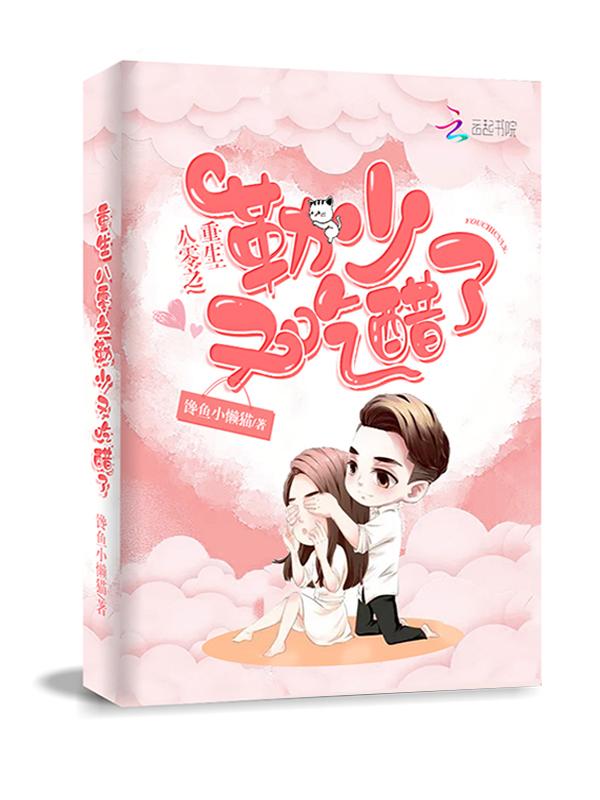秃鹫小说>真千金她靠穿越发家致富免费 > 第三十二章(第3页)
第三十二章(第3页)
风声嚎叫,对着她薄弱的身子示威。
坐下,“裴沫”失神地望着皇城,不再动弹。
“差不多到这里该结束了,或者说别坐在这里,回去拿把刀趁他们不注意全捅了,一个不留。”
裴沫想扶额,但是被控制着不能动,她深呼吸被寒风呛了口气,咳嗽间把自己多年来所听过的所有粗话在脑中全部回过一遍,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算了,按照那些字幕所说,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又何必浪费力气。
仅剩的暖气随着天色流逝,同时离开的还有她的生机,背靠枯树,几乎要分不清哪个才是自己。
大年二十九深夜的风太冷了,冷到她想离开。
风雪肆虐的人间,她盖上了暖和的被褥,周围放着火盆,里头是烧的旺的煤炭。
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纷纷扬扬的红色碎末忽地被风卷起,洒向皇城不远处的枯树,树下靠着一人,闭眼睡去,仿佛能透过尚残留的余温感受她醒时笑貌。
飞扬的红碎伴着漫天的雪,给她盖上了红白相间的厚重被褥。
枯树在冬日折去,没能等到春天。
“女儿不孝,往后恐难尽孝了,不能再留在这里惹得妹妹生气。”
裴沫睁开眼,又是这一句话,她皱眉,自己不是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为什么又重来?
再来一次她感觉真的会受不了,再下去,她真的会疯的。
天听感受不到她的怒意,对此不在乎。
“啪”
裴沫:“……”
又来,她想咬人,明白了当时的霍咎的心情,如今的她,仇视所有人,包括她自己。
又回到了逃婚这一天,她干气满满地准备钻狗洞的时候,发现身子
可以支配的时间变短了。
嫁人,高中,举杖欺人……
“裴氏你不过娇蛮无理,本想着让你自请下堂,如今死不悔改,我今日便休了你!”
裴沫先是委屈。眼中莫名淌下泪来,泪水溅落在手背,她不禁茫然。
她为什么会感觉委屈?
她想回程宅,为什么?
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扑门,还好尚余的理智挽留住了她,没有做出这些行为,眼中的泪蓄满眼眶。
她又一次死在二十岁,在大年二十九,在除夕前夜,疯嚎的雪次次为她盖被。
“恕女儿不能尽孝,往后会常常思念爹娘的,不能再留了,妹妹会生气的。”
往后每次走向“未来”,她可支配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少,直至没有任何可支配自己身子的地步。
最后成了封在木偶中的灵魂,看着“裴沫”一次次陷入泥沼,彻底死去。
她就这般一遍遍重复,随着能控制的时间越来越短,她能感受到自己逐渐融于这麻木的生活,不再反抗逃婚。
面对被程炝休弃,逐渐多了不属于自己的情感,从原来的古井无波还带着点小窃喜,如今她委屈,裴沫颤抖着手拂去自己脸颊上的泪痕,眼中的满目绝望。
多少次了,她记不清了。
几十次?
还是上百次?
若是真的有所谓的最后一次,死后能不能结束一切。
她,实在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