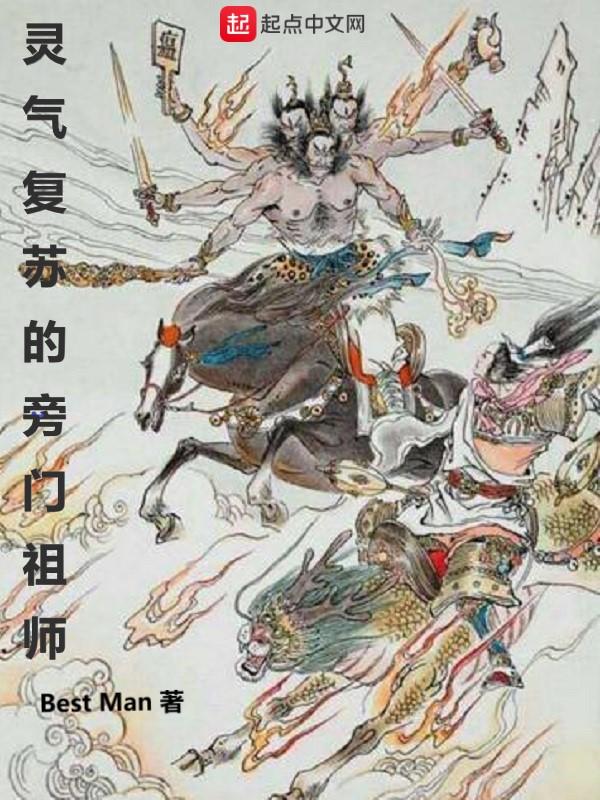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被拐以后我逃出来了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宋玉诚在她旁边,背脊挺拔,站得笔直,低着头看着她。“我们只是警察。”宋玉诚语气里微带疑惑,她客观陈述道,“犯罪人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是法律家的事情,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只需要验明尸体,找出凶犯,就可以了。”又是这样。刁书真有种一拳打在空气上的无能为力之感。“那林依依的父母,你不觉得他们太冷漠了吗?”刁书真愤愤不平道。“冷漠?”宋玉诚微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竭力理解刁书真的意思,“他们忽略了林依依受到的伤害,没有履行好父母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人是赵国华。”“现在林依依和赵国华都已经死了。既然她的父母排除了嫌疑,那么就与本案无关。无关之人,我们不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什么评价。”刁书真坐在地上,轻轻摇晃着自己的膝盖,像是在思考什么。“我说玉诚。”刁书真轻轻地说,“如果因为我是被杀死的无辜女孩,你会杀死凶手,替我报仇吗?”“杀人是违反我国刑——”宋玉诚愣了几秒,说道。“行了行了。”刁书真打断她道,“随便问问,不用当真。”她的声音带了些潮气,闷闷的,沮丧低沉,有点像是感冒早期。宋玉诚很是疑惑:难道在地上坐上一会儿就会着凉吗?黑暗之中,她看不清刁书真的表情,她有种伸出手去摸一摸的冲动,方能缓解心头莫名的慌乱之感。“够了。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关注下去的。”刁书真站了起来,衣着凌乱,满身尘土,无比狼狈。“但不是为了给赵国华那个人渣讨回公道。”刁书真说,“冷漠的父母纵容了作恶的禽兽,软弱的妻子成了罪孽的帮凶。喜庆的世间根本不会听到弱者的痛呼,大概她们还没来得及发声就被掐住了喉咙。”“送凶手上刑场之前,我只是想要问问她,看着赵国华挣扎着死去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刁书真望着宋玉诚的背影。她穿着白色的衬衫,哪怕经过了刚才的打斗,还是那般整齐干净的样子。就像是荷叶的表面覆盖有一层细绒,不可能沾染任何俗世的污泥。她身处红尘之中,却并不属于红尘。澄澈清明,俗尘不染。那样澄明无瑕的心境,是不会滋长刁书真心中那种如熔岩般的愤怒、死灰板的迷惘以及汹涌澎湃的悲伤。刁书真轻轻地叹了口气。她在这条泥泞不堪的路独自跋涉了太远太远,在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太久太久,疲累到出现了幻觉,以为身边有了同伴的存在。但宋玉诚和她,终究是截然不同的。两人并肩走出了空荡荡的校园,默然无语。惨白摇曳的路灯下,身后拖着的长长影子交叠在一起,显得亲密无间。但是影子的两位主人间,却似乎产生了一丝难以弥补的裂隙。鉴于c市接连发生了两起未破的命案,案情重大,犯罪手段残忍恶劣。她这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协助c市市局尽快侦破此案,缉拿凶手,防止下一起案子的出现。关于是否串并沿江风光带一案以及红星中学一案,因现有的证据不足,c市市局暂未采纳刁书真的建议,而是将两案进行分开侦查。虽然刁书真凭借直觉觉察到这两起案子中隐隐有某些微妙的联系,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能理解是很正常的。对此,刁书真并无异议。回到家里,桌子和地面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似乎是有经年累月没有人住过了。其实距离红星中学案发才过去了不到十天,刁书真却有种仿佛过去了十年的疲累感。她躺倒在床上,阖上双眼,两起案子的各种信息流从她的眼屏前闪过。脖子僵硬,眼睛酸疼无比,恍如某种紧绷无法松开的牛皮革。她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半点睡意。奔涌的思维在她的脑海里呼啸而过,她仿佛看到了孙凤娣和赵国华的扭曲挣扎的神情,耳边隐隐听到他们垂死的哀鸣。破旧的旅馆,昏黄的灯光之下,高大的影子压制在小小的躯体之上,随着身子的晃动,少女连珠般的泪水落下,如同破碎的玻璃。少女已经躺在小小的檀木盒子里,尘封在那个破落的墓园里,没有墓碑,没有人祭奠。像是一缕清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存下任何痕迹。本该记得她的人,或许欢欢喜喜地摸着妻子的肚皮,满心欢喜地等着新生命的到来吧。刁书真胃里翻腾起来,恶性的感觉翻江倒海般袭来。庸俗的喜气让她觉得恶心。无论是早年在临床之上,还是现在频频奔波于现场,规律性的吃饭是一件对于刁书真来说都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落下的慢性胃病,她早就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