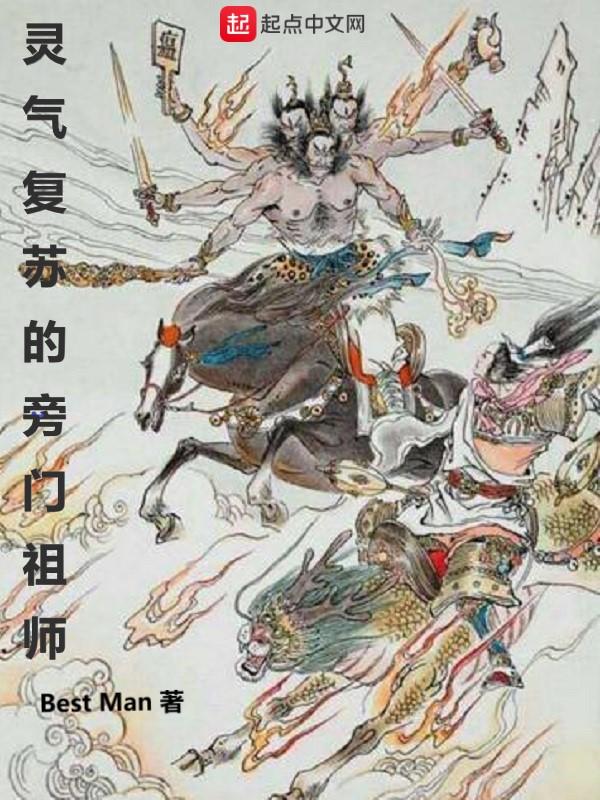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被拐以后我逃出来了 > 第26章(第1页)
第26章(第1页)
“看上去,赵国华真的是个兢兢业业的好老师了。”宋玉诚有些难以置信。刁书真坐了下来,她皱着眉头,缓缓拉开抽屉。宋玉诚凑过来一看,里面只有零星几个作业本,和一个订书机,别无他物。刁书真诡异一笑,手平伸进去,触到抽屉上方的顶板,随着双面胶被撕开的刺啦声,一本书赫然出现在了她的手上。封面粗糙,上面的女人身体□□,神色暧昧。纸张散发着一种盗版书籍劣质刺鼻的油墨味。刁书真挑了挑眉,指着书笑道:“我就猜到会有这么个东西。”宋玉诚不明其意,接过来草草地翻了翻,乍一看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她摇摇头,将书还给刁书真。“thestoryofo:untoldpleasures经典而有指向性的□□小说。”刁书真眼中迸发出兴奋的光芒,玩味地笑着,“看来我的猜测,并非是无稽之谈。”她看了眼自己的手表,指针逼近了十点四十五。她匆匆忙忙说:“算了,我回头再详细和你解释。我们先来模拟现场。”“还是我来当被害人,你来模拟凶手?”宋玉诚问。“不,这一次,我真正需要画像的,是被害人。”刁书真诡谲一笑,“只要能了解被害人,相信所有的疑点都会迎刃而解。”刁书真环顾四周,坐在赵国华的皮质椅子上,宋玉诚弯腰替她戴上眼罩。剥夺了视觉的情况下,其他感觉越发清晰敏锐,对方身上的冷香悠然袭来。她摸索着宋玉诚的手缓缓站了起来。赵国华一米八三,他是握着凶手的手,还是搭着凶手的肩膀?刁书真比划了一下,在心里模拟着凶手的大致身高。难道凶手只有一米六左右?刁书真摸索着,搭在宋玉诚的肩膀之上,慢慢地走下楼去。楼道里没有灯,本就伸手不见五指,更别提刁书真还戴着眼罩。两人的呼吸声在黑暗中清晰可闻。噗通、噗通、噗通,心跳像是密集的鼓点,在刁书真的胸口里回荡,血流在她的血管里奔涌。亢奋。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刁书真拉回纷乱的思绪,搭在宋玉诚的肩头,一阶一阶稳稳向下走着,忽然产生了一种希望这条路再长一点,长到这辈子都别走完的错觉。两人出了教学楼,踩过一阵平坦的地面,脚下变得凹凸不平起来,刁书真知道这是进入了案发现场的那片施工工地。她扶着宋玉诚的肩作为支柱,可惜地面上路障太多,她好几次都差点绊倒。宋玉诚停了下来。是到了赵国华尸体所在的位置。刁书真没有犹豫,像个毫无感觉的人偶,笔直地跪了下来,完全无视了粗糙的地面可能带来的伤害。她顺从地将双手背在身后,宋玉诚默契地将她的手束在一起,用扳手将钢圈和钢管拧紧。余下,同案发现场那样处理。恐惧使得刁书真有那么一瞬间的瑟缩和抗拒:她几乎就要站起来,摆脱束缚,将身后的人摔在地上,掐住身后人的脖子。不管她是谁,是敌是友。但她没有反抗。只是肌肉紧绷,神经紧张到了几乎要断裂的地步。她的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背上出了一层薄汗,喉咙干渴得像是要冒烟。在剥夺了视觉的,现在连行动力都被剥夺的情况下,活跃的想象力兴风作浪,将任何风吹草动都渲染成关乎生死存亡的信号。心跳恐惧,却又莫名刺激。这种将自我全部交托于她人,彻底失去自由,彻底沦为她人俘虏,任她处置的感觉——是如此的恐惧,却又如此甜美。一直以来,刁书真运用着他人眼中近乎鬼魅的天赋,一路披荆斩棘,屡破奇案。在旁人眼中,她仿佛手握神奇的钥匙,任何一个人的心门都无条件地为她敞开。她骄傲自负,不甘落后,就算在恋爱约会这种私事上同样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她披荆斩棘,在这条坎坷的路上,一个人背负着恐惧、愧疚、谎言和悲伤,在迷雾中走了太远太远。什么都可以不用想,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什么都可以放下,不用背负着责任。不用在大雨滂沱的天气,在泥泞不堪的路上,跌跌撞撞前行。没有自由,就没有随之而来的责任;没有自我,就不用为了活着苦苦挣扎。刁书真面上的神经仿佛灼烧起来,滚烫的热度融化了她的戒备。敏锐的观察、精准的推理、客观的判断,强大的理智在这一刻灰飞烟灭。她感到自己的孱弱,孱弱得如同罗网里的挣扎的鱼,毒蛇獠牙下的抽搐的猎物,祭台上供奉给残忍嗜血神明的美丽祭品,根本无从反抗,只能被动等待,在战栗的恐惧中迎接盛大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