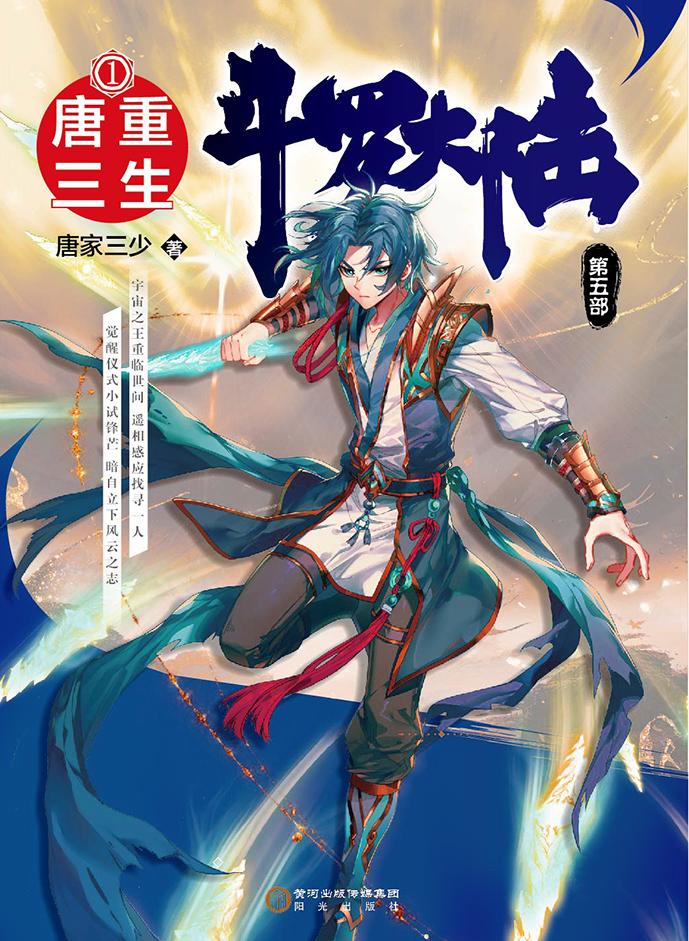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始乱终弃了清冷男主后 > 李家(第1页)
李家(第1页)
翌日,河倾月落,日高三竿。
秦知夷醒得晚,下楼用饭时,食肆里一个食客也没有。
账房先生在柜台边上打着盹,没瞧见小二春根,蔺九均也不知去哪了。
秦知夷心中疑惑,手搭在空泛的肚腹上,走进了后厨。
厨子罗大娘正在揉面,炖锅里不知道煮着什么,汤沸着顶起木盖来,咕嘟地叫着。
罗大娘见秦知夷来了,停了面板上揉搓的动作,热情地说道,“夫人起了?可要吃些什么,我现给夫人做。”
食肆的雇工都喊蔺九均为东家,而秦知夷是他的妻子,是东家夫人,是以大家伙都会亲切地唤她为夫人。
秦知夷应了声,只道,“今日不大想吃面。”
罗大娘一愣,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手的面粉,笑道,“夫人吃什么都使得的,这面团原是为了给春根做‘一根面’才揉的。”
“一根面是什么?”秦知夷纳闷道,“说起来,前厅怎么一个食客都没有,春根和蔺九均也不见人影?”
“贵人们都叫它长寿面,我们这样粗使的人没讲究,一根面的喊惯了。”罗大娘说着转身舀了一小瓢水,洗了把手,又说道,“听说要换新的供菜贩子,东家带着春根和刘芽一大早就出去谈生意去了,今天食肆就闭店一天了。”
刘芽是蔺九均请帐房先生时,一道雇来后厨帮闲的小子,秦知夷只约莫记得他个子还没春根高。
秦知夷了然,点了点头。
她心里却嘀咕着,也不知蔺九均是真有事,还是因着昨天吻得那样不知休止,今日太害臊了,特地寻了这个由头,一大早就躲着她。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昨日喝了点小酒,秦知夷当真不会那样冲动大胆。
但她喝酒从不忘事,也不会做自己不乐意的事。
罗大娘又问道,“夫人吃馄饨吗?这会下锅,等一刻就能煮好。早上大家伙吃的馄饨,汤底用的大骨汤。早市上的猪肉嫩,剁碎了包馅,吃起来很弹牙。”
秦知夷没什么特别想吃的,也就应下了,想起春根的长寿面,她又问道,“今日是春根的生辰么?”
“是呢,所以那皮猴子才央着我给他做长寿面。”罗大娘往灶下的添了一把柴,起锅烧水。
秦知夷问道,“总听你们喊他春根,春根姓什么呢?”
罗大娘看着锅里的水,还没烧开,只是微微冒泡。
她话中慈爱地说道,“春根没有爹娘,也就没有姓,打小是个野的,在巷子里吃百家饭长大的。”
秦知夷想起了什么,有些好奇问道,“春根是被拐来的么?”
罗大娘一面从盘里抓了十几个生馄饨进碗里,又将碗端放在灶台边,一面回道,“哪能呢,春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我是几年前逃荒来的,春根怎么没的爹娘,我就不清楚了。”
秦知夷心下微微惊讶,她平日不与食肆的雇工有什么交道,没想蔺九均聘的厨子和小二都是身世清苦的人家。
锅里水开了,罗大娘将碗里的馄饨下了后,突然问道,“夫人,您和东家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呀?”
秦知夷有些始料不及,“啊?”
罗大娘搓了搓手,有些羞窘地说道,“我和春根都是得了东家的幸,才能有地住,有口热饭吃,就想备点薄礼谢谢东家和夫人。”
秦知夷闻言轻咳了一声,“不必这样,你们都是正经做事领工钱的。”
不是秦知夷不想说,是她真的不知道蔺九均生辰。
生怕罗大娘又追问起来,秦知夷搪塞几句就离开了后厨。
她本想在楼下用过就上楼的,最后还是让罗大娘煮好了给她送上楼去。
经罗大娘一提,秦知夷也有些好奇起蔺九均的生辰来,。
她年初冬季末来的溪水村,这都又要过到冬天了,也没见蔺九均过生辰。
难道他是冬日里过生辰?
秦知夷起的晚,那碗馄饨混作早午饭一道吃了。
吃完后,她就窝在房里看话本子。
不知为何,话本子这会子倒是能看得进去了。
一两个时辰过去,话本子看得眼也酸涩,秦知夷打算下楼走走。
前厅里,蔺九均和春根他们还没回来,冷清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