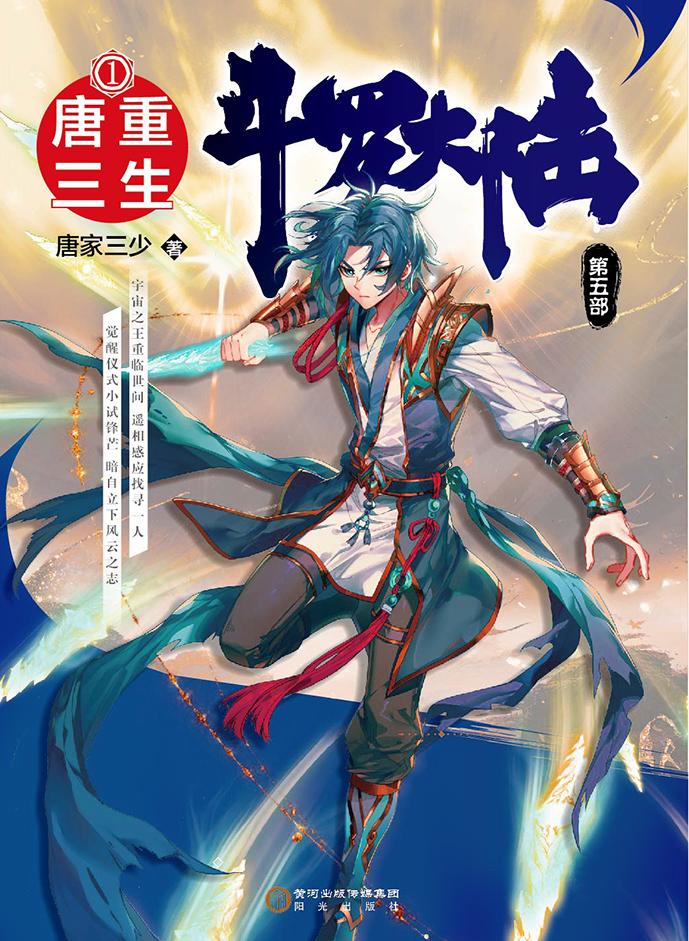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万人嫌反派重生后 > 第 16 章(第2页)
第 16 章(第2页)
迟珣又道:“我与霁云交好,视你也如半个妹妹。既然为兄为长,又怎会越过你去关心旁人。”
楚念声觉得有道理。
毕竟多数情况下,他比楚霁云更像她的兄长——她哥还是太严肃板正,说的许多话她都不爱听。
打从她刚进宗时就这样。
那时她因为试炼的事,和几个同门打了一架。对方被她打得奄奄一息,她也受了不少伤。
他们被送去医谷看治,不知道谁传出的消息,谷中医修都以为她染了疯症,不大敢靠近她。
唯有迟珣主动给她疗伤,还说她要真是有疯症,也正好看治。
概是看她年纪尚小,他又给她塞了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并宽慰:“要是疼,不妨玩些玩具分散注意力。”
她看了眼手中的拨浪鼓,稻草扎的小人,还有泥巴捏的娃娃,最后实在没忍住尽数往他头上丢去。
“你自己留着吧。”她说,“留着下山,再往北走三百里,那里有处学堂,里面净是些刚蒙学的小娃娃。你把这些给他们,权当收小弟了,日后他们还得喊你一声大哥,你还能自立门派当宗主。”
那些幼稚玩具被她扔得到处都是,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医谷弟子纷纷大叫:“传言不假,真染了疯症!”
他却还能笑出来。
“你倒比霁云好玩得多。”他摇着那拨浪鼓,“真不喜欢?那卖我的商铺老板可说,这是今年的新样式。”
“滚!”她骂道,剜了眼不远处战战兢兢的同门,“——看什么看!再看他摇这破鼓,我就摇你们,看谁摇得快些!”
但翌日迟珣替她换药时,竟提起她说过的话:“小师妹,你确定往北走三百里真有处学堂么?我昨夜里去看过,那里是百丈悬崖。”
向来肆无忌惮的楚念声头回陷入沉默。
这人什么来头?她随口一说的话竟还能去求证。
“找对了,就是那儿。”她没像昨日里那样气汹汹,虽然语气仍差,态度却有所好转,“你跳下去,那学堂就在悬崖底下的坟墓堆里,教书的叫胡夫子。”
旁边一人听见,忍不住在他离开时小声说:“师兄,别听她说些疯话。”
迟珣却不赞许:“怎就见得是疯话。”
那人惊诧:“这还不明显?什么学堂能建在悬崖底下、坟墓堆里头,这是人待的学堂吗?”
可又过一日,迟珣拎着根狐狸毛制成的笔,风尘仆仆地赶回,说:“虽然费了些气力,但好在找到了那学堂。原是狐狸一族,怪道在墓地上课教书。只可惜那位胡夫子说狐书不得外传,我没法看上一眼——但他送了这支笔给我,是为答谢那些送给小狐妖的玩意儿。”
她听见也没搭声,仅直勾勾看向昨天说她乱说疯话的那弟子。
那弟子羞得满脸通红,支支吾吾地道歉。
如今迟珣的年岁长了些,眉眼不像往日那般张扬,说话行事却还带着不管不顾的少年心性,诸多事上也仍旧包容。
-
想起往事,楚念声多少解了气,继续翻找起移行符,还不忘道:“那下回记得把话说明白,不然谁有闲心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倘若消气,现下能否说说缘何一人跑到这儿来?”迟珣稍顿,“是有谁惹你生气?”
“不是。”楚念声塞给他一张移行符,难得有耐心地胡诌,“刚才那两人,一个是我堂妹,另一个是我堂弟,我来看一眼——走罢,灵幽山洞里跑进来几条魔蛇,你正好去看看是什么来头。”
移行符催动,又一阵天旋地转。
刚才她走时,洞里还勉强有些光亮,这会儿却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
她打散在洞中踱步的幻影,用灵力凝出枚光球,引他去看那唯一一条还活着的蛇。
蛇被困在禁制中,不断扭曲挣扎。
她看着只觉得恶心,匆匆扫一眼就退出好几步,说:“留了条活的,兴许有用。”
迟珣打量着那条漆黑长蛇,随后掐诀,探出缕灵力。
仔细探查一番,他道:“这蛇并非是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