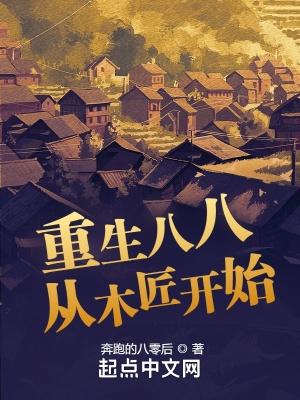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鬼灯的冷彻白泽腐图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啰、啰唆,你才拉低阎魔厅的水准咧!」末了在嘴里嘟哝了一声,似乎是骂了犀牛之类的词汇,但没敢太大声。白泽碰地从床上弹起,他蹦跳几下准备溜进厕所,推开挡在面前的男人:「换我洗了吧?走开走开,让我进去。」就在白泽准备把门关上时,用力推了几下却发现关不起来。以为门坏了往外一看,这才发现鬼灯正伸手抵住浴室门,另只手从半掩的门缝里伸入,塞了件旅馆准备的睡袍给他。他看向那只伸进来的手,忍住把门用力阖上夹死那家伙以报前仇的坏心眼,勉力从牙缝中挤出声谢,还故意用中文说。「不用谢,我只怕不先拿给您,等一下会看见一只白猪裸奔。」不知是否错觉,白泽仿佛听见对方低低地笑了一声,正准备反驳时又听见鬼灯充满恶意地补了句:「伤眼。」白泽气得把浴袍抢过来后,立刻用力地把门关起来夹那只手,可惜鬼灯的手缩得飞快,根本来不及夹到他。气得踢了一下门板表达抗议,却发现门板比想像中硬,没夹到人就算了还撞得他脚趾发疼,总觉得今天什么事都在跟他过不去,实在倒楣透顶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他哎唷了一声,委屈地泡进放满洗澡水的浴缸里头。水温适中偏热,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是很舒适的温度。每次都一下鞭子一颗糖果的,这就是上位者恩威并施的手段吗?好吧,好吧。绝对不是因为这招对他有用,而是他不想跟那个幼稚的家伙计较,他别扭的在心中投降。他轻轻摩挲着脚趾疼痛处,态度已经放软一半了。他把冻得红通通的鼻子泡进水里,看着泡泡一颗一颗的冒出水面。他想知道那个男人把手伸进水里触摸试水温时,用的是什么表情?明明是件小事且答案显而易见,那个面瘫鬼哪会有什么表情?但仅仅只是想着他,却想得浑身发热。更诡异的是刚刚听那些女优叫声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下身开始蠢蠢欲动,白泽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开始,已经满脑子都是那个恶劣的家伙了,而且还想到起了反应。这太奇怪了,这不可能。他把脚卷起来抱紧,头埋到膝上希望能缓解下身的反应。可惜非但没有缓解,他还想起了那个男人刚刚走出浴室时,深色的浴袍无法完整遮掩的,被热气蒸腾得有些泛红的匀称肌理。还有他们挤在车站厕所的狭小空间里,鬼灯以温热的口腔包覆着他的下身卖力舔含的事。想到最后鬼灯还刻意以湿软的舌尖摩擦铃口迫使自己在他口中射出时,那带着红妆的眼角上挑地性感模样。白泽将头靠在密布着水雾的冰冷墙面上,自我厌恶地啐了一口后开始用手抚慰下身。顺便催眠一下自己只是晚上受了点刺激才会这样,其实自己还是很喜欢妹子的云云。不过…总觉得这场景似曾相似,好像在地狱时也曾经泡在水里这么做过。他微喘着气,柔软的发丝随着手指灵活的动作在湿润的墙面来回磨蹭,沾粘在上头拖出几道黑色的痕迹。既视感在欲望前臣服,很快的他就只能把那些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事情抛诸脑后,思绪彻底沉沦。几声喘息后他释放出来,疲惫地将身体埋进浴缸里载浮载沉,彻底的自我检讨了一下。居然想着一个男人射出来,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接着又想到等会儿出去后还要面对那张脸,虽然他已经死了但还是觉得很想死,一点也没把握自己是否会做出不妥当的反应,万一反应过度被发现什么就不好了。于是就在他摩摩蹭蹭地吹干头发,正要打开门都还没碰到门把,门就碰地一声从外面打开,鬼灯顶着那张万年阴沉的脸直接踏进浴室。「要不是您已经死了,我几乎要以为您死在浴缸里准备破门而入了。」其实因为拟态药的关系鬼灯一直都觉得非常困倦,但他仍是强打起精神等那只洗澡慢吞吞的猪出来,结果一等居然就等了超过半小时,几乎快磨光他所有的耐性。只得焦躁地倚在床头跟睡意搏斗,忍住踹门而入的冲动。好不容易等到浴室传来吹风机的声音,却吹了老半天好像他的头发跟长发公主一样长需要整理很久一样,再也忍不住的鬼灯从床上跳起踹开那扇门。白泽因方才想着对方自渎而略为尴尬,不敢对上他的眼睛,面色微红地撇过头回道:「呃…有什么事吗?」「嘴巴张开。」鬼灯伸出锐利的指甲,轻轻划开左手食指及中指腹,血瞬间汨汨地冒了出来,滴落至纯白色的磁砖形成几摊怵目惊心的小血漥。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在厕所里的原因,就算血滴得到处都是只要用水冲干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