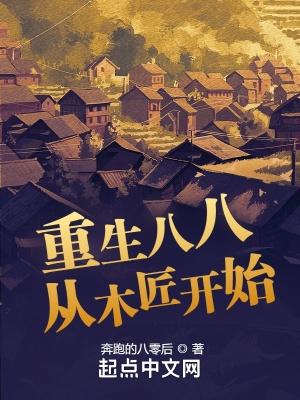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萌娃修仙 > 第16章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淋淋的人(第1页)
第16章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淋淋的人(第1页)
晁浩仁贱嗖嗖的晃了晃头,胖乎乎的脸笑得温和中显贱相,“敢不敢呢,本官都做了,你说呢?白当家的,你在怕什么?本官这也是为你好啊。既然你说这俩贼婆诬陷你,本官当然要还你清白了不是?稍安勿躁,先委屈你一小下下了。”说到最后,晁浩仁还用手比划了个“一小下下”的动作。白得钱气得咬得牙齿咯咯响,“我有什么好怕的?此事与爷无关,你少拿鸡毛当令箭。”说罢,狠狠甩了一下衣袖,转头指着挡在身前的衙役:“大胆,还不让开,尔等可知爷是谁?”小六子迅速从地上爬起来,蹿到他前面,指着他鼻子叫道:“我管你是谁,还我侄女来!不然,休想从这里踏出半步!”说罢,他“噌”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横在胸前,恶狠狠的盯着白得钱。白得钱眯了一下眼,眼中凶光乍现,“爷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起开!凡敢挡爷的路者,我白家决不会放过。”“哟哟哟,白当家的,我这个县令大老爷还在呢!你当着本官的面威胁本官的下属和治下百姓,这是不把本官当盘菜啊?时下州县的人,都这样猖狂了吗?”晁浩仁缓缓环视一圈,最后歪着身子回头对丁槐说:“本官头一次当县令,孤陋寡闻,丁师爷你给本官说说。”丁槐呼啦了两下手中的破扇子,随后用破扇子遮住口鼻,一双带着精光的大眼转了转,假装小声说道:“大老爷啊,我也是头一次到县衙当师爷,我哪知道县城的规矩这么多?啧啧,原来皇上任命的县令是摆设啊?到了地方还要听地头蛇的!”“咳咳咳。”晁浩仁似乎被丁槐的话给呛到了,不自然的用衣袖遮了遮脸猛咳了几声。而后瞅了瞅怒火冲天的白得钱,说道:“丁师爷啊,这看上去也不像地头蛇啊,倒是像……”晁浩仁停顿了一下,上下打量了白得钱一眼,“本官瞧着,倒是像土皇帝!”“你这个狗官,休要欺人太甚!”晁浩仁的话音刚落,白得钱便跳着脚破口大骂。他现在想走走不了,留下来又着急庄子上的安排会被发现,正急怒攻心。不想堂上那两人的对话,简直是诛心!让他瞬间失去了最后一丝理智。土皇帝?这名声可不能担!这是足以诛九族的大罪!“我堂兄乃当朝堂堂白侯爷,皇上身边一等一的宠臣。我堂侄女,乃皇上最宠的淑妃娘娘。更是为皇上诞下八皇子。你们得罪本老爷,可要想好了有几颗脑袋够砍的。”“哎呦呦,吓死本官了。”晁浩仁夸张的拍着胸脯往椅子背上靠了靠。白得钱一昂头,蔑视的看向晁浩仁。晁浩仁冷笑一声,清了清嗓子,坐直身子,正色道:“上述话语,你已经说过一遍了,不必再重复了。本官还是那句话,待查明真相,若真与你无关,自会还你清白。白当家的既然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何不在此等一等?”“晁浩仁,你,你敢这么对我,他日必将后悔。”白得钱咬牙说道。“噗嗤。”大堂外看热闹的人中,有人笑出了声。“笑什么笑?信不信我白家……”白得钱转头看向大堂外,恼羞成怒的迁怒他人。“我,我,我只是觉得县令大人的名字很好听而已,没有笑白老爷您的意思,真的没有。”那被白得钱盯着的人,立即摇手说道。陶凌晓看到这里,已经对县令的为人有了基本了解。这绝对是个和以往县令都不同的县令,他不畏强权,而且,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超好人。今天这事,即使不能动了白家的根基,也绝对能撕下白家一层皮来。想来,县令这一闹腾,那些衙役也该快马加鞭出城了。他跟陶予安对了个眼色,而后悄悄退了出去。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小妹说今天二哥会被人打断腿,不管是真是假,他都要去见见二哥。退出人群的陶凌晓,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朝武家武馆跑去。陶凌晓的二哥陶凌云,身材修长,长相俊美。在十一二的时候,就与陶予安一般高,像个大小伙,走在大街上就经常被姑娘丢花、丢手帕。而且,他极会读书,连陶予安都感叹他七窍玲珑。有一次陶凌云沐休,八岁的陶乐韵吵着要让二哥带她去县城玩。陶凌云本来约了同窗研习策论,但作为宠妹狂魔的他,爽了同窗的约带着陶乐韵进了城。也就是那一次,让这个十二岁的少年,断了读书路。他是被以调戏良家女、心思不正,取消了刚刚取得的童生资格,并被终身禁考。这当中发生了什么,陶凌云死活不肯说。他萎靡了一段时间,重新振作后,拜了县城武家武馆馆主武成龙为师,开启了习武之路。,!“呼呼。”陶凌晓一口气跑到武家武馆,扶着门旁的大石狮不停的喘息。“滚出去吧。”随着一声怒喝,一具人形物被丢出武馆大门,接着就是难听的谩骂声:“哼,果然是心术不正之人,卑鄙龌龊、下流无耻。仗着长得好,就以为人人都得:()修真渣呆萌娃换个位面专治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