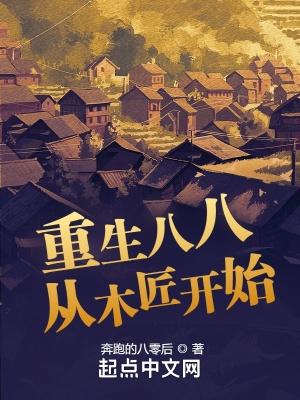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逆天毒妻萌宝陪我来重生 羽小灵 > 第367章(第1页)
第367章(第1页)
有人附和道,言语间对北冥候夫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北冥候夫人听着众人的赞誉,心中自是得意非凡,但她却故作谦逊地摆了摆手,笑道:“我若有那等本事,只怕连国师都要退位让贤了。”
正当众人谈笑风生之际,云汐领着张春如缓缓步入会场。
张春如经过一番精心打扮,脸上的脂粉虽厚,却也难掩她心中的疲惫与不安。然而,在这般场合之下,她只能强颜欢笑,尽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哟,这不是大将军的夫人和松言世子的平妻春如吗?”
安阳公主一眼便认出了张春如,连忙上前打招呼。
然而,刘尚书夫人却笑着纠正道:“公主怕是记错了,这位并非大将军的夫人,而是大将军的妾室。”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愣,纷纷看向张春如与云汐。
云汐见状,连忙解释道:“尚书夫人误会了,春如并非大将军的妾室,而是良晟世子的如夫人。”说着,她拉着张春如的手,一一向在场的夫人们行礼问好。
张春如虽心中苦涩,却也只得强作镇定,一一回应着众人的问候。“世子的如夫人?”刘尚书夫人闻言一愣,随即看向北冥候夫人,一脸疑惑地问道:“莫非是我记错了?我记得夫人之前曾提到过此事啊。”
北冥候夫人闻言掩嘴一笑,解释道:“你没记错,当时我确实是开了个玩笑。阴婚之事太过沉重,我便想着给大家找点乐子。不过我可没说过春如是奕寒的妾室哦,我只说她会入侯府为妾。我就知道大家会误会的,毕竟这侯府里可不止奕寒一个人嘛。”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北冥候夫人的一场玩笑而已。
然而,这场玩笑却在外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许多人都误以为张春如真的是奕寒的妾室。安阳公主闻言不禁嗔怪道:“你啊,真是胡闹!你可知道外头有多少人真以为春如是奕寒的妾室了吗?”
北冥候夫人却是不以为意地笑道:“那我就赢了嘛!我得入宫去向太皇太后讨赏去!”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与太皇太后之间的一场赌约。
太皇太后曾笑称她做事不用脑子,她便赌咒说自己若开一个玩笑,定能骗过所有人。
太皇太后不信,她便与太皇太后打赌,若她赢了,太皇太后便给她二百金作为奖赏。
没想到,她还真就赢了这场赌局。
华妮姑姑在一旁听着她们的对话,不禁摇头笑道:“你这赌注也未免太不公平了些吧?哪有这样拿别人的名声开玩笑的?”然而,北冥候夫人却是得意洋洋地表示:“管它公不公平呢!反正我已经赢了太皇太后了!”
吃亏
北冥侯府内,氛围凝重而微妙。北冥侯夫人特意将张春如请至府外,其意不言自明,是要让她亲眼见证一场精心布置的“误会”。
她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缓缓言道:“今日邀你至此,实为请你作为见证。众人皆误以为你乃奕寒之妾,这番话,你可是亲耳所闻。”姑姑华妮,在一旁听罢,不禁掩口轻笑,打趣道:“难怪太皇太后常言你脸皮厚实,既然如此,我便回禀太皇太后,说你明日入宫领赏去吧。”言毕,华妮姑姑轻摆罗裙,翩然离去,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在空中回荡。
北冥侯夫人望着华妮姑姑离去的背影,心中积压已久的郁闷仿佛瞬间消散,她畅快地笑道:“太皇太后总说我愚钝,这口气我憋了许久,今日总算得以抒发。”转而看向张春如,他故作关切地问:“幸如夫人,我方才的玩笑可曾让你不悦?”
张春如轻轻拽了拽衣袖,低垂眼帘,声音细若蚊蚋:“我哪敢有丝毫怨怼。”虽是如此说,但话中的不满与情绪,在场之人皆能感知。
众人皆知,张春如身为司马府千金,素以清高自诩,她心中所愿,乃是能得一威武武将正夫人作为归宿。
奕寒,正是她心中理想的人选,即便为妾,她也甘之如饴。
而对于赵松言,她从未放在眼里,更不屑于成为他的妻妾,即便是平妻之位,对她而言亦是侮辱。
她之所以愿意留在侯府,不过是为了寻找机会,一雪今日之耻,更是为了将那对她而言如同蝼蚁般的男女彻底击垮。
夜幕降临,云汐带着一抹难以言喻的愉悦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而此时,张司马的马车正静静地候在侯府之外,见下人护送张春如安然无恙地走出,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他走上前,仔细打量了妹妹一番,确认她未受丝毫损伤,这才松了口气。
“司马大人,夫人命奴婢转告您,她既已承诺不伤如夫人分毫,便定会信守诺言。”
下人恭敬地禀报着,言语间带着几分不以为意的放肆,“您若不信,大可亲自检查,看夫人是否信守承诺。”
张司马闻言,虽觉下人言语无状,却也无奈,只得淡淡回应:“代我谢过夫人对舍妹的照拂。”
“夫人还说了,谢就不必了,但请大人务必管束好自己的妹妹,以免她日后再惹是生非,到那时,恐怕就连大人都难以保全她的周全。”下人说完,也不待张司马回应,便转身回了府内。
张司马望着妹妹,心中五味杂陈,他沉声道:“上车吧,我们回去。”待二人坐定,马车缓缓启动,他才再次开口:“春如,你需明白,有些亏,是必须要吃的。云汐非等闲之辈,你我皆非其对手,还是安分守己为好。”
张春如听后,眼中闪过一抹不甘与愤怒,她紧握双拳,咬牙切齿道:“我为何要咽下这口气?即便是吃亏,也该是他们吃亏才对!”她的声音虽低,却充满了决绝与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