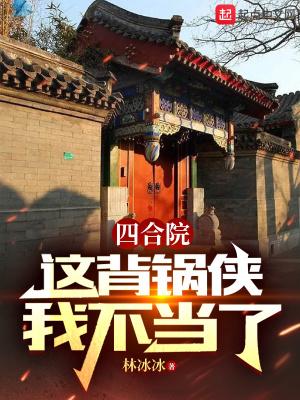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九零糙汉的宠妻日常 > 第47章 扎针(第1页)
第47章 扎针(第1页)
这边,宋忱推着林鹿到了洗手间,不像在家里那般自由,请了个女乘务员进去帮她。再回来时,林京北已经睡下了。又坐了两天,才将将到了沪市。几人没有第一时间就是朝着医院去,先找了倪大姐推荐的那家房东,租了一个月的房。这边很少短租,倪大姐找了好久才找到的这么一个,上次就一起告诉了宋忱。“屋子和家具都别弄坏,一个月后我来收钥匙,要是弄坏了东西押金我可不退啊。”先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又押了二十块钱在他手里。宋忱答应:“行,一个月之后保证你的屋子还跟现在一样。”大叔:“没事,我相信你。”因为他看了宋忱的退伍证。租好了房,吃了饭,三人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才去了中医馆。倪大姐说他家人特别多,要早去才能抢到号。宋忱他们七点到,这会儿前面已经有人在等着了。可见竞争是如此的激烈。八点半中医馆正式开门,现在人已经排到了十几米开外。林鹿一家排在第三个,前面的人看完,宋忱推着她到老中医周爷爷跟前。有人说他们家祖上是皇帝的宫廷御医,医术十分了得,全国各地有啥疑难杂症的来找他治一下回去就好了。周爷爷已经是八十好几的高龄了,蓄了一把胡须,看着很是医术高明的样子。林鹿把手伸过去给他诊,老先生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一家三口实在是一句都没听懂他说得什么。不过,有一点很确定的是他诊出了林鹿之前遭遇的事,连她大概啥时候醒的都知道。他跟旁边跟着的学生周福海说了句什么,随后那人起身拿了一“卷布。那东西拿过来过来,打开一看,是各种大小粗细不一定要针。周福海交代:“可能会有些痛,你们家属按着些,我师傅要开始给她扎针了。”他的话虽然不像老中医那样口音浓重,也还是带了些的,且语速过快,宋忱两父子只回到了关键词——扎针、痛、按着。痛确实痛,是一种麻木皮肉被玻璃扎到底的尖刺痛,语言很难描述,林鹿只能说比直接扎在她脸上还难忍。额头冒起了冷汗,上牙紧紧咬着下牙,担心自己会溢出痛呼声。宋忱捏着她的下巴迫使她松开牙齿,把手臂送过去,小声说:“痛就咬我,别咬到了你舌头。”林鹿难受至极,咬不了牙齿只能咬上面前男人乖乖送上来的手。他手臂上瞬间起了一个带着红血丝的牙印,林鹿也没尝到了铁锈味。林京北抿着唇,一言不发地看着,然后出去打了一瓶热水回来,在盖子里带了半杯,送过去:“漱一下口吧。”林鹿眼圈红红的,顺势漱了几口林京北倒的水。林京北又把几张纸递过去:“吐在里面。”照顾完她喝了水后,才出去扔垃圾。周福海忍不住说道:“你们一家关系真好。”林鹿疼得没力气说话,宋忱淡淡道谢。持续扎了两个小时的针,这一天才算是过去了。周福海交代:“她这情况特殊,我师父说隔一天来扎一次,扎满三十天就好了。”意思是他们家要在这边待上两个月才算是扎完。既然开始了第一天,他们也不会放弃。反正房子已经租好了,煮饭啥的也方便。回去后林鹿就回房间休息了,宋忱交代林京北在家看着林鹿,他去菜市场买点粮食和菜。还有锅碗瓢盆。宋忱做事快,动作麻利,去菜市场一趟,不仅把粮食和菜买了,锅碗瓢盆也挑好了。他一个人拿不了,花一块钱请店家帮了一手,送到门口。回家时看见母子俩都在看书,宋忱没打扰,一个人钻进了厨房捣鼓。城里不用村里那种灶,贵的电器更是买不起,做饭的工具就是一个小火炉。宋忱以前在部队时,也轮岗在炊事班帮忙过,生火做菜炒饭对他俩说就是小菜一碟。昨天父子俩已经把家里打扫了一遍,厨房可以直接用了。宋忱小小露了一手,炒了两个菜一个汤。菜是老中医写的食谱(医嘱),应该说是他让她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宋忱完全遵照他的医嘱来。饭菜端到桌上,唤道:“吃饭了。”放下围裙,回房间看了下,发现——在他做饭的这么一会儿,林鹿就眯了一觉了。窄小的脸颊上沾满了自己的口水。宋忱开玩笑:“梦见什么了,吃得这么好。”林鹿:“梦到你给我做了好吃的。”宋忱信她个鬼话。“走了,我们去吃饭吧,给你做了你梦中的菜。”二菜一汤,林鹿一道菜全给包底了,另一道一筷没动。宋忱跟个老父亲一样劝道:“医生说这个也要多吃点,你多吃几筷。”林鹿撇嘴:“可是我不:()九零之糙汉厂长的心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