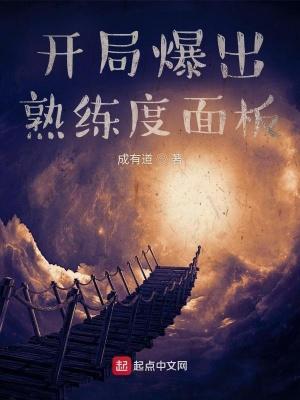秃鹫小说>大司马请客 > 第167章(第1页)
第167章(第1页)
帐外突然一阵嘈杂。
他凝神听了一阵,抬手解开顶部遮布的系带,待舆图完全被遮住,这才回身到案前坐下来。
文信侯越黎疾步入了帐,面上还带着惊慌不解之色。
“原来是越侯,有失远迎啊。”时彧忙起身行礼,做了个请的手势,“快请坐。”
“传闻说陛下下旨,遣散了玉人军,原来竟是真的?”文信侯哪还顾得上坐,回想刚刚入营时,看到那一排排空空如也的营帐,不可置信道,“司马大人就没想想办法,任由那赵镇逼着陛下胡来?”
时彧见状,自顾自重新坐好,轻笑道:“越侯说笑了,既然是陛下的旨意,时某哪有不遵的道理?”
“都什么时候了,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文信侯焦急道,“恩师年迈,这么冷的天,日日守在宫门口,人都昏厥了好几次,这么下去,恐怕…”
时彧打断道:“那越侯该去寻医工。”
文信侯撑案坐下来,苦着脸道:“我知道,你与恩师之间,有些误会,可事到如今,也该摒弃前嫌,一致对敌了。那帮缩头乌龟,无人敢站出来公然反对赵镇,任凭恩师一人挣扎。若不趁赵镇掌权未稳,及时出手,恐怕日后想要撼动他会更难。”
“在我赶回长安之前,玉人军已经被遣散了。”时彧摊开双手,“如今我与越侯一样,是个名不副实的空头侯爷,越侯凭什么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出头鸟呢?况且就在我南下之时,朝堂上弹劾我的声音还不绝于耳,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拥护我。”
“可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时彧轻笑,“越侯说得轻巧,拿什么试,我的命么?”
文信侯“蹭”地起身,愠怒道:“想不到,司马大人竟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时彧也不恼,“越侯行比伯夷,此时不在宫门口与云老太公一道,反而在我帐内,是为何?”
“你——”
“是因为,越侯也知道,这所谓的对敌之策,根本于事无补,可若在此时,还不做些什么,又枉为正直清流之辈。”
文信侯被他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呼哧呼哧喘了半晌,也没憋出一句话来。
扶桑入帐添茶,时彧又作请的手势。
文信侯把头别向一边,“哼”了一声。
“我从不属清流,也就没越侯的烦恼。”时彧端起茶盏轻吹了吹,抿了一口,“现如今,陛下人在赵镇手中,不顾陛下性命强攻,定是不妥;齐齐站在宫门口声讨,隔靴搔痒,亦是无用。”
“按司马大人的说法,这也不行,那也不可,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赵镇颠覆朝政,什么都不做吗?”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时彧道,“越侯还是想办法,劝云老太公注意身子吧。”
文信侯终于忍无可忍,拂袖而去。
时彧独自端坐喝了会儿茶,扭头问扶桑,“少夫人那边,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