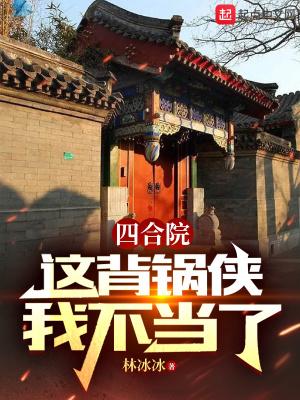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踹了渣夫后她宠冠六宫了 作者桐盏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利用可寡妇门前是非多,前来求亲的,……众妃嫔瞧着太后对长宁长公主满是关心的样子,顿时是各有心思。大家久居深宫,对于当年沈家获、罪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不清楚。可太后娘娘,却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可见,太后娘娘到底还是养尊处优惯了,觉着姜家会一直屹立不倒呢。姜太后把众妃嫔的神色看在眼中,只见她轻抿一口茶,也不再继续方才的话题,而是转而提及了接下来太子选妃的事情。承宁帝不动声色的转着手上的白玉扳指,道:“母后心里可是有了合适的人选?”姜太后听了只笑着道:“这些日子,内务府倒是拿了贵女的花名册给哀家看,可哀家到底老了,瞧着这些如花一般的姑娘,一时间竟也没了主意呢。”姜太后如何能不知道,眼前这母慈子孝也不过是假象罢了,她自然也不敢全权操、控了。甚至,她不得不承认,如今在面对承宁帝的时候,她其实已是失了些底气。毕竟,眼前的承宁帝已非刚登基那会儿,能继续任由自己摆布。想到自己如今连区区一件太子的婚事都不能全权做主,太后也不得不感慨,自己当真是老了,岁月不饶人了。而等到众妃嫔从慈宁宫离开,姜皇后却是和姜太后诉委屈道:“姑母,您方才也瞧见了,这昭贵妃如今是愈发不把姝儿放在眼中了,故意送了绣了鸳鸯的荷包给皇上,这不是让姝儿颜面尽失吗?”见她竟还在纠结这桩小事,姜太后直接就板起脸来,“不过一个荷包,哪值当你这样委屈。如今,太子选妃才是大事,你怎就这么拎不清呢?”姜皇后非但没得了姜太后的安慰,反倒是被训斥了,瞬间更是红了眼睛。见她这个样子,姜太后顿觉头痛极了,直接便打发了她下去。等到姜皇后离开,姜太后吩咐窦嬷嬷道:“给哀家拿了丹、药来。”窦嬷嬷听着这话,却是有些犹豫道:“娘娘,这丹、药虽是好东西,可吃多了,怕也伤身。”可没等窦嬷嬷再劝,姜太后便一把摔了手中的茶杯,耿耿于怀道:“方才什么情形你也瞧见了,皇帝如今和哀家,不过是剩下表面的母慈子孝了。可偏偏,皇后是个蠢的,这些年,竟然没有丝毫长进。你说,哀家能不担心哀家百年之后,皇帝便愈发没了忌惮,对姜家动手吗?”“所以哀家,绝对不能服老的,便是撑着最后一口气,也绝对得亲眼看着太子登基。”窦嬷嬷侍奉了姜太后这么些年了,如何能不知道自家娘娘想什么。而这丹、药的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护国公不知在哪里偶遇了一个道士,而这道士,竟声称是珏山老人的传人,掌控了长生不老的丹、药。护国公原也不信,可半信半疑间,好奇心驱使护国公便试了半个月的丹、药,结果,护国公竟感觉精神劲儿好了许多。也因此,便把这道士悄悄请入了府中,更时不时差人送了丹、药入宫来。太后娘娘原也不信,可她到底老了,便是日日喝着太医院弄得大补汤,精神劲儿也大不如前了。所以,便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思,服用起了丹、药。结果便是,太后竟有些离不开这丹、药了,一日里不服一粒,就觉着缺了些什么。这些,窦嬷嬷看在眼中,却也急在心里。要知道,这史书上也不是没有皇族追求长生不老,可结果,又有几个善终的呢?可窦嬷嬷也知道,自己劝不住自家娘娘的,所以也只能起身去拿了丹、药来。姜太后服用过后,顿时感觉身上轻松了许多,不过,她也不忘吩咐窦嬷嬷,“这丹、药哀家吃着,似是愈发有功效了。可越是如此,这道士的事情,越得瞒着众人的。”“尤其,绝对不能让皇帝知道了。”姜太后说这话不是没有缘由的,本朝一直尊佛法,道教根本没有立足之地的。而且,皇上本就愈发容不得外戚,若让皇帝知道护国公府养了道士暗中炼、丹,岂不越发坐实了护国公府的狼子野心。可姜太后绝对想不到的是,这道士的事情哪需要她故意瞒着承宁帝了,这道士,本就是承宁帝故意给姜太后送的大礼。却说这边,承宁帝出了慈宁宫,长长的宫道上,承宁帝想到方才慈宁宫的一派祥和,眼中瞬间尽是冷意,问戚海道:“这几日里,护国公可还是依旧送了丹、药往太后宫里?”戚海躬身回禀道:“皇上,确实如此,不过,奴才瞧着,这几次送进来的丹、药,比之前多了一倍不止。奴才估摸着,这该是太后娘娘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