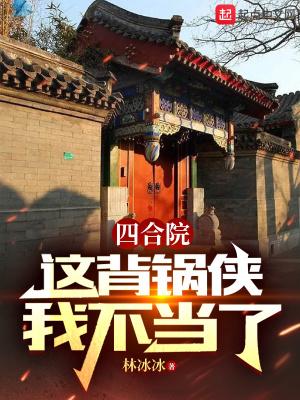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在惊悚直播中爆火 > 第47章 无路可逃(第1页)
第47章 无路可逃(第1页)
雾并不太厚,一个中午的时间让雾气散去了些,视野范围在百米左右。桑榆甫一踏进雾里,一阵森冷的风吹得她打了个哆嗦。刚午后一点过,体感温度却低得仿佛夏日深夜。她远远望去,隔着灰白色的轻纱看见了田垄之上的人影。她站在民宿前的空地上,正前方是一片又一片的水田,田间小路站着许多分辨不清是男是女的身影。如果忽略掉过分寂静的环境,那么眼下的灯笼村是桑榆来到这里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见村里这么热闹。距离她最近的一个黑影微微垂着头,桑榆凝视着他,分辨出它的手部动作。它在打电话。这个看起来人性化的动作安在它身上显得很伪人。桑榆没有靠近。她踏进雾里本就冒险,确定雾中的东西不会突然像丧尸一样向她发起攻击之后,她便稍稍放心了些。桑榆望向广场的方向。灯笼村在山谷里,广场地理位置靠里,在山麓地带,往广场后面再走走,便可以看见被土黄色的泥土与矮树覆盖的山体。她要先去找徐阮,c组的这位不是新人,她不怕死,甚至她可以用死来试错。和徐阮合作甚至交换信息是最不亏的买卖。但她的想法很好,真要实施时却立即遭受到了阻碍。因为前往广场的那条田间小径和水泥小道全部都站着那些绰绰的人影。有的低着头,有的仰着脑袋,像民间常有的纸人木雕,随葬的那种。出于安全考虑,桑榆没有过度靠近。但是目前来说,除非她走水路,从田间庄稼旁走过去,但如果绕过这条路,广场和山间依旧有黑影,她也一样功亏一篑。站在空地上思考了一会,桑榆抬腿往来时那条小路走去。那条路上没有黑影,两侧田垄倒是立着许多,与其他方向的道路完成不一样。像是……有什么东西走过,它们自动让了道,退回到两侧。桑榆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下雨,土路上的水洼干涸了许多,但泥土依旧湿滑泥泞,一路走过去,桑榆又脏了一双干净的鞋。她想试着去看看村口。如果没有看见王皓,她会试着给他打一个电话,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尽管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当然,比想象更魔幻的是现实。桑榆看见一抹模糊的红色光芒,在道路尽头的地面上。雾气降低了可视范围,但桑榆依旧看清了那抹光芒来自一盏放在地上的灯笼。除民宿之外,又一盏点亮的红色灯笼。桑榆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站定,这时她已经看清,那盏灯笼旁半蹲着一个人。她的身边有一条黑影,乌色的液体流淌在道路上,桑榆嗅到了淡淡的铁锈味。剪刀的咔嚓声清脆,她裁剪着,又用锤头敲击着什么,发出令人牙酸的响动。这个距离,只要桑榆有任何动静,她都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周围更是没有庇身之地,桑榆轻轻呼出一口气。“……你好?”见她一直在忙碌着,桑榆主动出击了,人声在灰白色的天地间颤动着,蹲着的那个人动作猛地一顿,随后她扭过头,和桑榆撞上视线。“你是……!”看见她的脸的那一刻,桑榆有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并不出众的外貌,扁平的五官,凸起的额头,甚至眼尾那点痣,这分明就是当时电话里徐阮说过的那个人!女人呆呆看着她,忽然低头看了一眼腿边那一条东西,赶在桑榆再开口之前从喉咙间吐出一声刺耳的惨叫。这叫声仿佛桑榆马上就要拿着刀杀她一样,简直比杀猪还惨。桑榆被吓了一跳,讪讪地张了张嘴,哪知女人连灯笼都不要了,拔腿往远去群山跑去。桑榆还记得徐阮说过,这个女人曾经提着刀要杀她,按理来说,该跑的人分明该是桑榆。眨眼间女人已经以一个不同于常人的速度跑得不见了踪影,深深埋没进了群山与雾气之中。桑榆只好暂时放下困惑,往那盏灯笼走去。待走近后,她才看清那躺在地上的一条东西是什么。躺在路上的人是个熟人——王皓。他已经死透了,乌色的液体离得近便能看出殷红的色调,他的腹腔被掏了个大洞,头部也鲜血淋漓,整具尸体破碎异常。不过自从见过了桂梦佳被林聂先暴力破坏过的尸体之后,桑榆只觉得王皓的尸体还算整齐,不幸中的万幸。红色灯笼泛出的光芒照得他破碎的脏器无比鲜艳,仿佛市场小摊上打上光的猪肉。但桑榆嗅到一点腐臭味,蚊蝇肆意在他的尸体上飞舞,他应该同样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强行离开灯笼村的警告明晃晃地摆在这里。桑榆疑惑地变成了另一件事,关于那个女人。她拿起灯笼,纸皮灯笼内的蜡烛跳动着,桑榆看向它的上方,一簇橘红色的焰火不安分地跳动着。桑榆抱着灯笼研究,回忆着嬢嬢们组装灯笼时的步骤,连蒙带猜的操作将放置着蜡烛的下盖打开。放在那里的是自制的蜡烛,比矿泉水瓶盖大一些的银白色小蝶装着约莫只有四分之一的凝固红蜡。伴随着烛火的燃烧,烟味和不知名的腐臭气味涌进桑榆的鼻腔,呛得她咳嗽了一阵。这不是普通的蜡烛。制作过程中,必然加入了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桑榆看向王皓,地上还残留着他的内脏碎片,以及一把剪刀,一把杀猪刀,都沾着暗红的色调。王皓应该早就死了,在他死后,女人提着灯笼来到这里,剪开他的衣服和皮肤,用杀猪刀开始剜割他的脏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桑榆看见她之后,她夺路而逃,放弃了这盏灯笼,也放弃了这个进行到一半的工作。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桑榆飘忽的目光又落到王皓的脑袋上,须臾之间,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汇。在古代有一种酷刑,叫点天灯。:()救命!我在惊悚直播间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