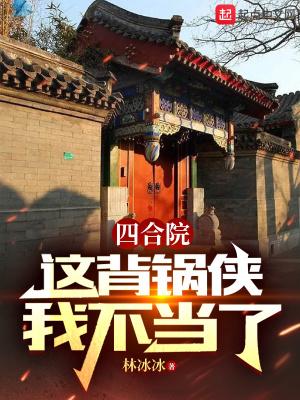秃鹫小说>罗勒鸳鸯番外篇 > 第54章(第1页)
第54章(第1页)
“您说,我向您诉说罪孽,我要忏悔,神就会宽恕我。”“这句话我向每位来这儿的人都说过。”“我有个兄长,我为他动情。”女人紧张不安地交握双手,“您说我错在乱伦,不在欲望。”“我记得您,”伯珥想起来了,是晋铎后第一位来向他来告解的女信徒,“之后再也没听见您的声音。”“是的,我没再来过了。您说的话我每时每刻都牢牢记着,我尽量避免和兄长单独相处,还央求父亲为我寻一门婚事。一年前我从女校毕业的时候,父亲介绍了现在,管理一六九八四四八五七。的丈夫给我,我们很合得来,当月就举行了结婚典礼。”“听起来很幸福,您已经从兄长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不,请您听我继续讲。”直到现在,女人的声音始终平静,“我母亲身体一直很差,在我结婚后不久就病逝了。她走得突然,当时只有我陪在她身边。”女人突然不说话了,过了一会才徐徐开口:“她枕头下有一张没写完的遗书,原来…我是收养的小孩。”“在母亲葬礼那天,我看着合上的棺椁,看着不断堆积的褐色泥土,看着掩面哭泣的哥哥,只觉得是自己躺在坟里,他们把我的爱情埋了。我爱她,可我本性难改,我无可救药。我做出这辈子最大胆放肆的决定。那晚我赤裸爬上兄长的床,我抱他吻他,既兴奋又难过。”伯珥发现女信徒交握的手松开,他问:“您的兄长是怎么做的,同样抱着您吻上您,完完全全接纳您,还是推开您、辱骂您?”女人没说话。“我想是前者,不然您不会来教堂向我诉说。”她接着说:“…他埋在我胸口哭,他疯狂压着我。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他握着我的手腕从后面操我,他在低吼,我根本分不清里面的哭声。眼泪啪嗒啪嗒落在我们交合的地方,我很疼,也在哭。”“酣畅淋漓,哭累了,做累了,我们才沉沉睡去。那晚我梦到火焰,好多好多火焰,一簇簇的,一会儿看起来无害可怜,仿佛随时都会塌陷。一会儿又尖锐逼人,要堪堪刺入我的身体。我不断逃、不断逃…长出翅膀飞到天上,或者长出犄角钻进地里。所有人对我避之不及,爸爸妈妈,曾经爱我的人。”“您愧疚难挡。”伯珥说。“可是我突然落在某个人怀里,火焰熄灭,我睁开眼。兄长搂着我入眠,他脸上有泪痕,我一口口吻没了。”“我以为这样可怕的噩梦不会再找上我,直到我发现自己怀了孕。丈夫和婆家欣喜接受,从那天开始,我每晚都梦到自己被烈火烧死,我惊醒,身边躺的不是哥哥,而是我的丈夫,那种不可言喻的虚空又在清醒的时候吞噬折磨我。”“我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想过就这样一了百了。我实在卑鄙拙劣、自私自利,却又无比懦弱,女人犯的罪在我身上应有尽有,上帝不要我,魔鬼不留我。”女信徒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她的指甲紧紧抠着洞口,伯珥能看出她战栗不止。“我受够了,神父,受够了…”“好姑娘,好姑娘,”伯珥竭力想要安抚她的情绪,他轻轻把女信徒抠得通红的手指掰开,“请把手给我。”伯珥握着的手在大幅度颤抖,手背手心尽是未干的眼泪,“您永远是父母的好女儿,兄长的好妹妹。”“禁忌是绝对公认的,僭越无论如何都要受到惩罚,然而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让人受罚,才是最为深重的僭越。乱伦也好情色也罢,都是要把我们带入极端状态的东西,带给我们幻想与欣喜,却也在无声地向我们施咒,它要我们痛苦,要我们纠结,要我们永生孤独。这就是您的心结,上帝没在惩罚您,而是您自己在惩罚您。”伯珥看向窗外,夜幕开始啃食大地。如果问神父以前他从没有想过如今会做的事情,那恐怕就是和什亭疯狂的一切和现在坐在聆听亭里对他的女信徒说:“上帝也有妻子,上帝也会做爱。”“情欲是孤独的产物,而往往越神圣的人就越孤独。”他总结。最后一位了,可神父习惯再等等,他站起来对着窗外伸懒腰。伯珥神父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再等等呢,哪一刻他在等,每一刻他在等。刚才的女信徒让他想起乌别和阿卜斯。乌别和尤利娅耽美肉裙扒医思榴捂期灸翎灸,的女儿出生在一个周六的清晨,隔天傍晚邮差送来报纸,阿卜斯的名字被写在失踪人员栏下,失踪等与死亡,这众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