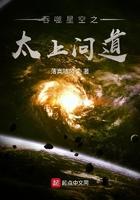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柳丝长简谱 > 血迹与笑容(第2页)
血迹与笑容(第2页)
“可不,先习惯习惯,怕什么,去了那儿,你们也是上等货。”
趁他们说话不备,柳乐猛挣开,一头撞出人墙,跑出几步转头想帮计晴时,她已被半推半拽拉入门里了。
常琨并不着急,对着几人说:“你们先去好生招待她,等我再劝劝那个。”
柳乐抓起裙子回身就跑,一眼瞧见前面一道门开着,门口站着人,正张望。她心想这里住的全是恶人,不论被拉进哪里都逃不脱,无暇细看,发足向巷外奔去。眼见跑出一多半却被常琨追上,狠狠揪住胳膊。
“跑去哪里?都是咱们自己的宅院,无人到此处来,跟我走罢!”
正拉扯时,巷口传来马车声,两人都转头望去,见一架黑色马车,由两匹健马拉着,旁边随着几名骑马侍从,正往这边拐。
柳乐大喜,一面在常琨身上扑打一面呼喊救命。常琨紧紧拽住她,满不在乎道:“谁家的车回来了?这一片没不认得我的,整个京城的人全知道常大爷!这是我家门口,当真嚷嚷出来,也是你背着丈夫与我私会。”
他见车子靠近,益发要使他们知道,省得来管闲事,于是满嘴里大声说:“乖乖儿,莫使性,饶你这回,早跟爷回去,还有你的好处。”
马车照常行驶,侍从们也端坐于马上没有动作,柳乐的心快要沉下去了。谁知车行到跟前却又停住,从上面跳下一个男子,弹弹衣袖,负手走来。
柳乐一眼看见那人威严的模样,心头一宽。能得救了,她高兴地想。——来人不是别个,是那位晋王。他见过她,应该还认得出。柳乐不怕有人会听常琨胡说八道,只怕再来一个又是他们一伙,这下她放了心:虽难说晋王是多么正直的人,但他自负身份,总不至于跟这些淫恶之徒为伍。
常琨也瞧见了,不敢再逞性,只将柳乐推在身后,一手拽住。柳乐甩开胳膊,站住匀匀气。常琨见她不喊不闹,以为自己的威胁奏了效,心里有几分得意,面上堆出笑容,趋礼上前:“不知王爷下降敝处,失迎,恕罪!”又套近乎说,“小弟贱名常琨。王爷还记得上回陆将军府上摆席吃酒,当日小弟也在。这是小弟的第三房下,平时多惯了她,惯得忒狂了,没大没小,为一点子事便与我合气,跑了出来,王爷见笑。”
晋王面无表情走上前,挨近常琨时,忽地拽住他胳膊,往前一扯,再一推。柳乐看见常琨趔趄着朝后倒了几步,脸皱成一团,喉里喘着粗气,手捧上腹——那里多了一柄刀,刀身看不见,暗金的刀柄顶端,嵌着一块椭圆的青金石,长夜瀚海的蓝色与沉静。
要不是常琨痛苦的样子绝非虚假,这真像是在城隍庙前耍的一套把戏,接下来就该听见连串的喝好声了。
柳乐茫然向四周望了一圈,几个侍从都木人似的立着。她想喊却喊不出——常琨该死,可她不明白怎会有人一语不发就动刀?
晋王低头看常琨,开口说了句:“不巧得很,我记得她,不记得你。”
常琨瞪着眼,喉中咯咯作响,挣着直起身,向柳乐站的地方挪了两步,手握在刀柄上。晋王忽地一步迈在柳乐身前。鲜血四溅,柳乐不由探头去看血从哪儿洒出来。
一声闷响,她看见常琨一只脚在地上蹬了蹬,看见他的衣服沾满了血,看见他灰白色的眼睛向天空翻着。
柳乐感到自己在后退,但是腿脚又仿佛不是自己的。“过来,别看那个。”一只手在她背上托了一下,她扭头,看见晋王。
他的脸被溅上了几点血,胸前也有。可是可怕的是他的眼睛,只有把取人性命看作家常便饭,对生死完全无动于衷的人才可能有这种眼神。
柳乐浑身一颤,哑着嗓子喊道:“快去救人,计姑娘在——”
“你过去看看。”晋王松开手,对一位打扮与他人稍见不同的青衣侍从道,“不要吓到计姑娘。”
侍从去了,另一人拿出条帕子,从水囊倒水来沾湿,捧给晋王。他拿起来漫不经心在脸上抹了抹,又低头在前襟上抹了抹,轻巧随意地一丢。“收拾了。”
两名侍从上前,一人抬头,一人抬脚,把尸首抬入车里,又一人捡起地上的匕首等物收了,从腰上拔出刀,用刀鞘把渗了血的地皮翻起来,血迹埋到底下去,用脚踏实。不足半盏茶工夫,一切处理妥当,丝毫看不出此处刚发生过血淋淋一场命案。
晋王这时候冲柳乐笑道:“你帮我瞧瞧,还有没有?”
柳乐气息未平,闻言一惊,向他脸上望一眼。一张脸干干净净,干净得唇边的笑炫目如艳阳,她没想到他会这样笑。
柳乐这才看出他天生的威势,不敢再看,目光移到他身上:他穿一件靛蓝圆领缎袍,胸前只有两道擦拭留下的水迹,看着并不显眼。
“没有了。”
晋王也把她略一打量,“不必担心,你身上没沾上。不过这衣服回去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