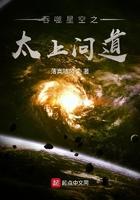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听说胖子没有腐权盘搜搜 > 64番外美丽新世界(第3页)
64番外美丽新世界(第3页)
“被你搞糊涂了。你们队不就是你、越总、丁大佬三个人,哪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你记错了吧,要不就是麻醉打多了,医生!医生!来帮这个人看看!”
苏岘从床上挣扎起身,把这个战友推开,赤脚奔出,敲开每一个有战友的病房,重复问他们:“逾明去哪了?”“你怎么可能不认识宁逾明?”
最后他被医生和护士架回了病房,浑身发冷、牙齿打战。
所有人都失忆了。要不就是他在做梦。这里不是现实,是他在战场上失去意识后的幻梦。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
疯了吧。
可是不管睡去几次,又从梦中醒来几次,其他人都没有恢复正常。
有战友问他:“你要找的到底是谁啊,真没人认识。”
不,还有两个人,一定认识。
越亭风是目前的异能强度最大的异能者,大概被单独关在哪里,和丁当一起战后消失了。
不久后,软禁解除。
苏岘发动了所有关系找那两个人,大家都感叹他们小队真是情比金坚,纷纷援手。
最后他堵在一家研究所门口三天,如愿见到了丁当。
“他去哪了?”
他们都知道苏岘不是在问越亭风。
“你真的想知道?”丁当胡茬一把,眼神疲惫。
苏岘狂喜:“你果然也记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丁当给了他一叠照片,苏岘瞥到表面的那张,手一抖,照片洒了一地。
——每一张,每一张都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缸,无数光纤从缸外插入缸中的营养液,连接到中央的人脑上。
苏岘从喉咙中发出短促的,断续的悲泣。
他已明白这人脑属于谁。
苏岘的心理医生评价他——极易陷入极端幸存者愧疚中的自毁型人格。
苏岘想过呀,像另一个世界中的自己那样,把余生用在行善育人之上,直至死亡。
但是做不到。
因为这失去亲友的痛苦根本就不是他妈的什么幸存者愧疚。
苏岘战后回了校园教书,因为他最喜欢叫他苏老师。
一天一天,一月一月,痛苦并未随着时间变淡一分一毫,苏岘有点撑不下去了。
他下课后一时间不知去何处,也许去天台吹吹风吧。
终端机突然响了。
聊天工具里的四人小群中有消息弹出来。
里面有一个名字永远不会亮起来,苏岘每看一次,心如万仞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