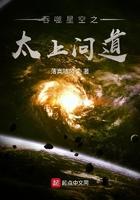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找错反派哥哥后笔趣阁 > 第55章(第2页)
第55章(第2页)
钟宴笙敏锐地感觉到,从雁南山回来后,淮安侯和侯夫人的心事似乎都很重。
是他也无法帮他们调解的沉重心事……甚至他们的心事,似乎就是与他有关的。
是他的存在,让侯府为难了吗?
钟宴笙心头飘过这个念头,静静地想着,坐在对面,好奇地问:“听说爹爹当年高中探花,打马游街时,许多官家千金在楼上招手,您一眼就看到了娘。”
淮安侯摸了摸胡子,脸上难得多了三分笑意:“嗯。”
钟宴笙抿嘴笑了笑,心下复杂。
淮安侯与侯夫人感情极好,这么多年了恩爱如旧,一定也非常关爱他们的孩子,可如今他在侯府,他们的关心也不得不分成两半。
俩人皆有心事,路上无言,到了河边,云成等人放下东西,便退去了马车边,只留俩人在河边。
淮安侯熟练地上饵,将钓竿递给钟宴笙:“垂钓需心如止水,哪怕几个时辰没有动静也正常,切忌焦躁。”
钟宴笙戴着草帽,坐在小凳子上,抓着钓竿“喔”了声,心想是不是该继续说说定王殿下了?
淮安侯也握着钓竿坐下来,看看身边眉眼漂亮的小儿子,又望向平静无波的水面,似乎是察觉出了钟宴笙对萧弄的消息格外关注,慢慢接上了之前在府里的话题。
“定王府曾经盛如繁花,尔后迅速凋零,只剩两个血脉。如今陛下盛宠,隐隐势如从前,萧弄不是蠢人,当是有把握全身而退的。迢儿,你觉得他如何?”
钟宴笙听得正认真,猝然被问到,没反应过来:“什么如何?”
淮安侯的目光笼罩在他身上:“萧弄。”
钟宴笙不知道淮安侯怎么突然莫名其妙问他萧弄如何,正想回答,手上的钓竿突然剧烈地动了起来。
河面有了波澜,钟宴笙眼睛一亮:“爹,鱼上钩了!”
淮安侯皱眉教训:“运气罢了,戒骄戒躁。”
将那条上钩的鱼提上来放入桶中后,父子俩继续垂钓谈话。
钟宴笙琢磨着淮安侯的问题,硬着头皮回答:“定王殿下,人挺好的?”
淮安侯:“好?迢儿,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
钟宴笙手上的鱼竿又动了:“爹!鱼又上钩了!”
淮安侯看了眼自己一动不动的钓竿:“嗯。”
在淮安侯的协助下将鱼捞上来后,钟宴笙比划了一下,更兴奋了,眼睛亮晶晶的:“爹,这条比之前那条大!今晚让厨房做酥骨鱼吧?另一条可以炖汤,娘喜欢喝。”
“……嗯。莫要喜形于色。”
钟宴笙听话地收敛了下笑意,把鱼放进桶中,又坐了下来:“爹,我们说到哪了?”
淮安侯停顿了片刻,道:“萧弄并非完全如外人所传那般做事随心所欲,他心机极沉,不好相与,你往后若与他相处,定要提起警惕……”
“爹,鱼竿又动了!”
淮安侯捏紧了纹丝不动的钓竿。
这心快谈不下去了。
钟宴笙注意到淮安侯面色有异,有一丝迷茫:“爹,您不是说,垂钓要心如止水,静心凝神吗?”
淮安侯沉默片刻,面容冷肃,挤出几个字:“萧弄年纪大你接近一轮,不是好人。与他相处,谨慎一些。”
钟宴笙悄咪咪想我干吗要跟他相处,但看看淮安侯的脸色,还是乖乖点头:“好,我会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