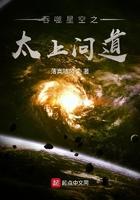秃鹫小说>六州歌头刘过 > 250260(第7页)
250260(第7页)
待那声音消失不见,他才愕然回神,抬头望向对面的床铺。
一只伶仃的手从被底挪出,苍白的指节正试图抓住床沿。
“今行!”顾横之失声叫道,忙起身欲奔过去。
却不想腰佩一扫,带偏了晾在砚台上的毛笔,笔锋挟着浓墨在纸上滚了一圈,污了他才列下的优缺。他忙去扯那黄纸,毛笔洇到底下的干净纸页,他又忙去抓毛笔,乱糟糟的沾了一手磨。
他看着这场面愣了一下,干脆将手里的纸笔全都扔进纸篓,不要了!
贺今行已用右臂撑起半身,长发凌乱铺在肩头,面色淡如生宣。
他抬眸,看着他几步跨到跟前,嗓音微弱得像拂不动水波的风。
可他在笑,笑他:“何故这样急?”
顾横之忽地平静下来,擦净了手上的墨,半跪在床前,扶他靠坐在床头,“我怕你没有看见我,强撑着起来,伤到自己。”
他一边说,一边替他放好软垫,掖好被角,才出去兑了杯热水。他在外间备了个小炉子,正为此时。
贺今行的目光随着他的背影走远,收回来自然地将这屋子扫视一圈。
半开的窗扇透进一斛阳光,窗下的半月桌上,一枝木芙蓉沐光舒展,如置身春天里。
真好啊。
他不自觉用右手按住左肩,手掌包裹住臂膊,慢慢下滑。一层薄衫之下,藏着明显凸起的纱布。
“今行。”顾横之唤他回神,将杯盏递过来,眸光落在他的手臂上。
他松手去接,慢慢地喝下半盏,交还的时候说:“没关系,还能活动,只是不太能用力。”
一用力便觉绵密的痛楚。
顾横之将杯盏握在手里,“可以慢慢地养,一定能养回如常。等战事结束,我们去赤城山,找唐神医,李太医……”
“横之。”贺今行看那只盏快要被捏碎了,截住对方的话,“我不怕失去一只手。”
“很值。”他说,“就算废了一双手,能换铸邪怒月一条命,也是值的。”
顾横之坚持:“可我觉得不值。”
贺今行不说这个了,再次抚上左臂,挽起宽袖,指尖碰到纱布缠绕的结,“你替我换的药?”
顾横之没想到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一时语塞。
贺今行就笑,解开那个结,将纱布一圈圈地卸下。
顾横之抬手虚覆在他的手背上,没有立时按住,而是祈求似的询问:“今行?”
“我只是看看。”他很坚决地拆完纱布。
顾横之便收回手,和他一起,仔细端详那因剜去一块血肉而形成的凹陷。
直到他说:“这是否算身有残缺,在不得为官之列?”
那只杯盏终于在崩溃前,被顾横之放开,掉到地毯上。
陶瓷碎裂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他替他换了好几回药,因此看过他的身体。
他知道他受过许多伤,手臂,胸膛,肩胛,腰侧,腿腹,新伤叠旧伤,将肌理分割得支离破碎。
他看那痂痕的新旧,便能往前推出受那道伤的时间,十五日、三个月、一年、两年……
再想起那些时日他所在的地方,西凉,秦甘,宣京,江南,汉中……
山河万里,烙印在他一身的伤疤里。
“不。”他看着今行的眼睛,反驳他,认真到虔诚:“很漂亮。”
这三个字犹似掷地有声,令四目相对的两个人如冰雕一般,久久不语。
直到卷着尘埃的风在眼前乱舞,贺今行才心下一颤,带着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自心底拔出一个徘徊许久的猜测。
“你是不是……”他才张口就觉得自己冲动了,还是昏了头的那种冲动。
下一瞬,脑海便被“既然昏了头,那就昏到底”的念头彻底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