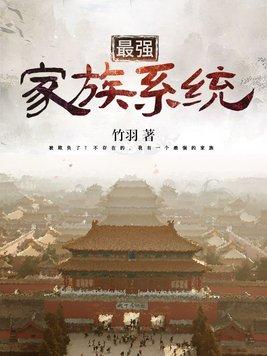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闰年上半年有多少天 > 26(第2页)
26(第2页)
司闻以单手攥住她双腕,另一只手解下领带,将其手腕紧紧绑住,猛力一拽,周烟受力扑向他。他适时弓腰,瞬间封她的唇,辗转缠绵。
周烟猝不及防被舌头堵住退路,却迅速适应。
司闻点到即止,扯开她,看着她微红的唇说:“不要跟我讲条件。”
真是斤斤计较。周烟没理他,只想挣脱开这条领带。司闻不许,拽着领带长端,往更明亮处走去。
周烟像个罪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执法人员带出案发现场,可司闻又一点也不像正义的人,他才像罪犯,像一个成语:狼子野心。
周烟笑了,肆意而笑。
司闻未闻其声,却知道她在笑,这感觉很怪。
他带她走过了车,周烟挑眉,问:“不回家?去哪?”
司闻:“吃饭。”
周烟想起冰箱有吃的,说:“回去我给你做?”
司闻停下,周烟撞在他背上,撞得鼻子生疼。
司闻扭头:“我非得吃你做的饭?不能吃别人做的?”
周烟不吭声,她也没有很想伺候他,毕竟他也没给她开保姆工资。
司闻把领带扔给她,说:“拿着!”
周烟拿着领带,笑容消失。
司闻见她不高兴了,忽有些触动。
四年来,周烟在他面前更多时候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她所有有趣的神情、行为,都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就像他先前在耳机里听到的,她应对别人的靠近时的机灵,就不曾对他展现。
偶尔她喝多了,或者哪根筋没搭对,会在他面前露出一些,可都如昙花一现。不像刚才,她竟然在闹脾气,在他面前,清醒地、很明确地闹脾气。
周烟越过他,走出两步,没感觉人跟上来,扭头看他,果然还在原地。她也没说话,站着等他。
司闻回神,转身继续走,路过周烟时牵起她。
周烟一惊,低头看,确是被司闻牵着,不解地想,难道他想牵领带却牵错了?但她没问,他也没有解释。
两个人走到护城河,过桥时,小贩冲他们大声吆喝:“十块!二十块!”
周烟偏头看一眼,小贩跟看到商机似的,上前推销:“看看戒指!都是真钻!”
周烟没买过钻,但有十块钱的真钻?就问对方:“玻璃制的?”
小贩拿给周烟一个,热情地道:“水晶制的,看着跟真钻似的,二十块钱,也不贵,要一个吧!”
周烟拿手上看了看,觉得不喜欢,又还给他了。小贩不死心,后退两步,张罗着让周烟再看看:“那看看别的,看这发卡,你戴准好看。”
周烟拿起一个发卡,别在头发上,问司闻:“好看吗?”
司闻没说话,不过他的表情分明在说:丑。
小贩看周烟感兴趣,更卖力地推荐:“姑娘你本来就长得好看,别上这发卡,显得更好看了。这位大哥不喜欢,你可以戴给别人看啊。”
司闻从周烟头发上把那破发卡摘下来,扔给他,说:“她敢。”
小贩原本还有满肚子奉承话想说,看到这人沉着脸不好惹的模样,管住了嘴。
司闻没了耐性,将周烟拉下桥。
下桥后,周烟的眼睛也不停歇,在歧州最大的平民夜市四处张望。
司闻停住,她也被迫停住——
她的手还被他牵着。
她看向他,想问怎么了,他却抢先摘下袖扣,掀起她一绺头发穿进去,又穿一回,将其固定在她刚别发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