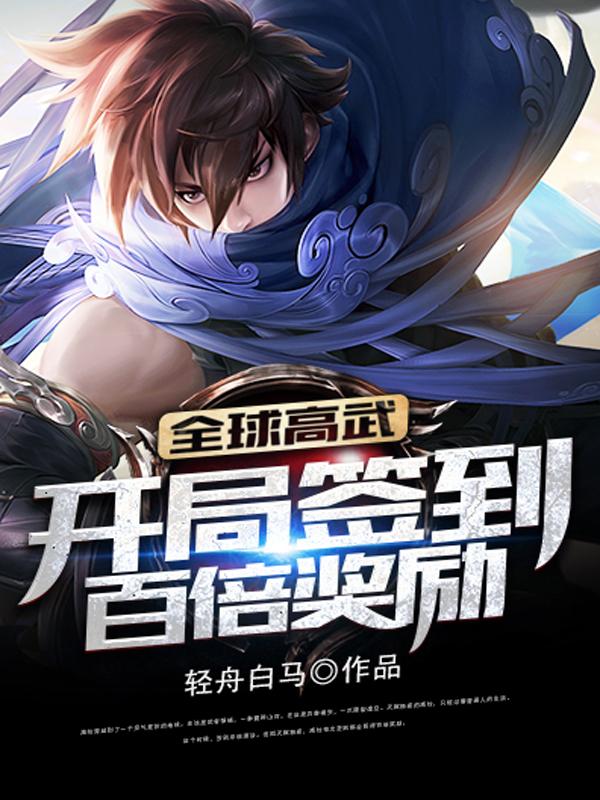秃鹫小说>买活无防盗格格党 > 12501260(第10页)
12501260(第10页)
一个是对外的公用笔名,一个才是对内登记归档的真实姓名,《买活周报》接纳外部投稿时就是如此,是允许投稿者采用笔名的。如此一来,只有自己人知道,到底谁占用了每年的多少篇幅,外部想要从这些地方来抓小辫子,却是没有那么简单了。
“或许也是没有想到吧—我们是站在如今来看从前,自然觉得破绽很多,接近于匪夷所思了。可要想到,《周报》开办,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哪有公开图书馆这个概念?
每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前几年也必然是新东西,倘若还是把书籍当成是珍贵的难得之物来看待,那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被查档的后果,报纸就如同邸报一般,发过也就完了,谁能想得到作者?
更不会有人想到,自己可以凭借报纸而一跃成为名流,这报纸的威力,也是随着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买地的疆域越来越大,而逐渐彰显扩大的。这个过程,恰好和我们长大的时间一样,是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常识,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也能更好地利用和接纳此物,但对沈主编那辈分的人来说,这是个新东西,琢磨起来总有些滞涩,怕是不会和我们一样,运用自如,考虑问题,也就没有那么周全了。”
顾眉生思前想后,也就只有这样的理由,勉强能解释得通了—那周报刚创刊的时候,只怕填满版面都是难事,合格的编辑也很难找,发表文章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宝贵的机会,反而是一种回报不多的负累。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能力的编辑多负责版面,这根本无可非议,能找到人来干活才是第一位的—如果对于编辑这个岗位的认识,始终停步于此的话,那自然也不会觉得吴江的编辑多发文章,有什么好指责,有什么好需要遮掩的了。
也不好说沈主编是否就是做如此想的,这才留下了这个堪称致命的破绽。同时也要看到,周报前期,主管的人还是六姐,沈主编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这才慢慢算是攥住了主编的权
力,在她上位的过程中,必然也要仰仗同气连枝的编辑来帮忙。
如此尾大不掉,在坐稳了主编之位后,不能及时切割,反而放任党羽开枝散叶,在《买活周报》内牢牢扎根,这也算是文人的通病了—心慈手软,讲究义气,宁可和这些肝胆至交同进退,也不会过河拆桥。
这实际上不能说是性格上的缺陷,就算现在,顾眉生、董惜白诸女之间,不也一样是交情甚笃,远胜金兰,倘若有一天彼此要互相割舍,她们真能狠得下心吗?
这样一想,便更能认识到世事兴衰之中蕴含的某种客观规律,是人力难以扭转的。虽然整理出了针对沈主编等人的利刃,但几人却谈不上快意,反而有些唏嘘,董惜白不禁念道,“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是《桃花扇》的结尾,也是近年来流传极广的一套古戏唱词,南腔北调都有配乐的,还有人别出心裁地配了西洋乐器来唱,虽然民间还是喜欢小调,但在有品位的居民中甚是流行。顾眉生几女自然知道出处,窦湄道,
“未见他起朱楼,如今却是要把他的楼推了,实在是不忍得—一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架势都摆出来了,台阶也铺好了,走不走,已经不由自主,可叹是这个把柄也太大,步子也太快了一点,只怕我们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出头挑了事,却得不到什么好处!”
她这道理是显然的—要说卢马姬抛出这个钩子之前,没有自己先做过调查,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这个钩子可能就是张利青主编刻意留下来在此时发动的。既然话都抛出来了,窦湄等人哪有不接的道理?
而这一接可好,问题太严重,很可能会促使沈主编以极快的速度下台,而此时以窦湄派这些才女的资历,根本不可能在沈主编下台后的人事动荡中,获得什么好处,她们不过是运营了几个月的报纸,而且还是隔了蔡东家、黎蔷这一层,要说接过《周报》的担子,就算六姐敢用她们,她们敢上吗?
这三五年之内,沈主编下台的话,接任的人选不做他想,肯定是张利青副主编,窦湄等人是被她当枪使了,这一点从她们统计出数据结果后,各自都已经明白,但箭在弦上,反驳的文章也还是要发的。只能希望张利青手下没有足够的自己人,一个卢马姬却不堪用,届时也要借重她们的力量,如此,她们也就算是打开了在《周报》上的发声渠道,有了引导民间舆论的资格。至于说接张利青的班,这个更是后话了。
在文艺界做得久了,见惯的是文人雅士之间的争风吃醋,稍微一卷入政治博弈,便不由得为其中的惊涛骇浪而咋舌,胆子小的,打起退堂鼓,渴望回到从前那悠游宽裕的生活中去,也是人之常情。不过,王而农对此却是不以为然,直言道,“想要把自己的思想态度,烙印在历史背景之中,就要耐得烦、吃得苦、忍得痛,这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天下间哪有送到嘴边的饭?在买地,一切收获都是劳动换取的,想要非凡的收获,便要有艰苦的劳动付出。而我等所求的,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和收获?倘若没有极高的觉悟、极大的付出,又何能厚颜祈望如此的成就?”
“休看沈主编的下场,或许令此时的诸位感到凄凉,但她的工作,她的思想,已经留在了这厚厚的报纸合订本中,将会被大图书馆永远收藏,成为后人考据这个时代最权威的证据。她所得到的,是‘表达的机会’,这已经远远胜过同时代其余天骄了。如张宗子、钱受之、张天如等文坛领袖,固然其成就各有侧重,但以文人身份来说,在历史上的厚重度,不如她。”
要特意点出文人身份,自然是因为张天如在立法界也有影响力的关系。至于张宗子和钱受之,这两代文坛宗师,当然也都凭借自己的本领,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也有过一些成功的作品,但在王而农看来,张宗子的地位要远高于钱受之,便是因为张宗子赶上了买地崛起的周期,他有这个时运。
一买地崛起时,他年龄尚小,融入得也好,有过一系列非常成功的采风报道,而这是钱受之所不如的,钱受之的学问固然是好,琴棋书画戏样样都来得,来买后,也有过很成功的戏剧作品,但他的作品里,“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观点,这便是旧朝老人,固有的问题了。他们原有的东西,和买地是格格不入的,一旦要表达自我,就容易不讨大家的喜欢,为了回避冲突,就只好什么都没有,或者勉力鼓吹一下买地这里极表层的东西。”
此人因为平时沉迷于学问的关系,对于生人相当腼腆,在琴棋书画这些雅好话题上,更是只能枯坐,报以微笑。可一旦谈到他所感兴趣的领域,便是侃侃而谈,而且语气极为自信肯定,“这样说并非是在臧否前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也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贡献。
二十年前,正当我买地新风乍然兴起之时,相对于当时普遍的抵抗和反感态度,持中而立、回避冲突、寻找共同点,这已经是难能可贵,超出时代的进步立场了。
这般的持重,在当时也是最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如此徐徐图之、润物无声、水滴无声,数十年下来,才有如今我们的许多共识—一以我们如今默认不分男女都要出外工作,不分性别都对家庭持有同等权利义务的认知,去批判二十年前,前辈所鼓吹观点的乏味胆小,这是何不食肉糜。
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也有一代人需要呼吁的进步,二十年前的进步,已经是如今的保守了,本来么,机体的新陈代谢,也是正常。沈主编一干人,在二十年前是进步的,这不妨碍他们在如今已经过于保守。
这是极感伤而又极无可奈何的一点—人往往很难随时代而往前发展,他们会一直停留在出现于时代中的那个位置,刚出现时,他们站在时代前头,现在却已经落后了半步。于是他们的位置,就要由另一批比时代风气要更站前了半步的年轻人来取代了。”
王而农言下之意,自然是指他们这帮新道德人士,以及窦湄几女了,他喝了一口清咖,随后蹩了整眉毛,明显对这种时新的饮品不太适应,将杯子放到桌上,略微推远了一些,这才肯定地说道,
“既然我等有幸成为了这样的人,那么,将前辈恭请下台,便也是时代赋予我等的使命。与其为沈主编唏嘘凄凉,倒不如从她之殷鉴中,反照自身,思量着当如何在时代的前头站得更久一些,别犯前辈犯过的错误。”
三女听到这里,也不由得对视几眼,都意识到自己此前也是小瞧了‘新道德”党人,这一党人中,固然有许多夸夸其谈,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才子,但也绝非俱是庸才。至少眼下这个新生代,果然就担得起他们的重视和依赖。看来,在沈主编倒台后的风浪中,她们是多了一批竞争者,想要踏上舞台的,并不只是张利青、卢马姬,以及她们这些个云县旧人了。
甚至可以说,王而农在很多地方,反而走在了她们的前面,以至于虽然窦湄等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但在之后所得到的好处,或许还没有王而农等人多呢,至少,王而农的准备明显是充分的,思考也比她们要多。
他说的有些问题,三女没有想到,甚至一时半会也给不出自己的答案—譬如说,王而农认为沈曼君的最大弊病,也就是“没有自己’,而这一点其实也是她们的弱点:“前一代,少有自己的声音和主张,一味寻找的只有调和。新道德者,不论如何他们的主张是已经浮现出来了。我们想要寻求的,究竟是报纸所代表的权势,还是其真正的发声的作用呢?我们是想要把握住发声的渠道,还是也有强烈的声音要发出呢?”
“倘若只有前者,那么,有我们没有我们,又有什么区别?或许,这也是沈主编数十年来,颠扑不破的另一个原因吧。想要权势的人有太多了,可有声音,有态度可以发出的人,劫远远没有那么多见。”
“而我们所信仰的,所想要发表的,那强烈的、明确的,我们认为应当属于时代旋律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第1260章云县旧女的困境
“不以出身论英杰,既包括任何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英杰,也包括,并非是某一出身者就特别不能成为某行业的英杰。正所谓内举不避亲,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包括了不因为乡情、师生情谊而特意避嫌,反而削减了这些人在一个行业的发展机会吧?
试想,如今造船业中,出身福建道泉州、橙城一带的工程师极多,再往下便是循县的船舶工程师,某一行当,从业者多为同乡,并非说明其中存在人情关系,只能说明人杰地灵,关于这个行当的教育氛围,在当地较为浓厚,年轻人也自然多往这个方向发展。
更何况,《羊城小报》上的统计口径,也是有所偏顾,有意地用日式文人’,来和''吴江同乡“进行混淆,把两者统一在一起呈现了,笔者这里也有类似的统计图奉上,却是区别了吴江和其余乡籍,如是便可以看出,吴江同乡的积分,也不过是刚刚过了两干而已,在万余积分中,不算显眼,其中更有沈主绵多年主管报纸的贡献,这样看来,炅江乡籍的编辑,谈何把持了《买活周报》的大权呢?
伪若是要说起,其余乡辑和沈象的关系,那就更要看到一个确实的数学问题了—一诸位年轻的读者,或许对于旧日朝的日子,已经淡忘了,不知道从前敏朝统管天下时,借大的国象,识字率不超过10%,而这其中多数还是相当于如今初级班、扫而班毕业的文化水准,有资格参考科举的人群,那就更少了,绝不会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