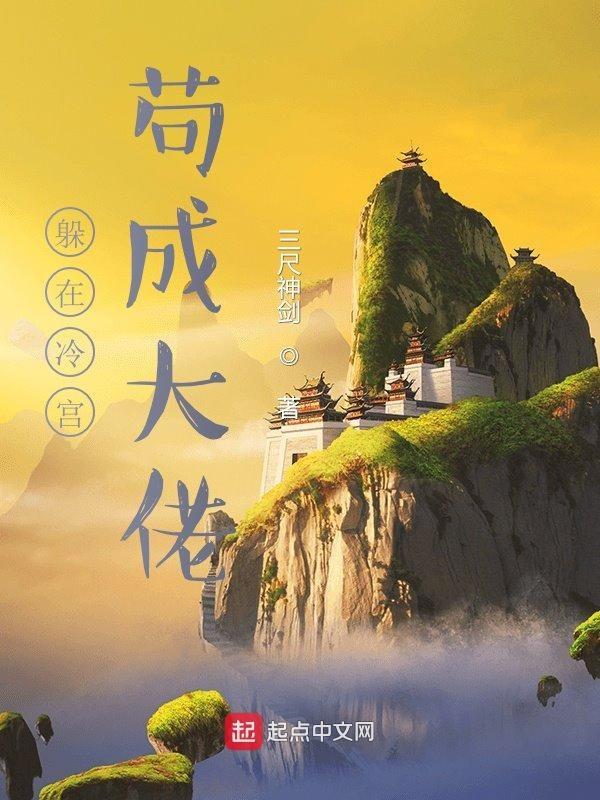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民国之南洋明珠小胖柑笔趣阁 > 第26章(第2页)
第26章(第2页)
余嘉鸿满脸为难,欲语还休,像是下定了决心:“管家,安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应该心里有数。安顺不是一个没有孝心的孩子。自古忠孝难两全,他劝不动郑老爷,只能带着亲娘离开。”
叶应澜听他话里有话,郑家跟日本人做交易的事不是刚刚查清,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不怕打草惊蛇?
管家脸色大变:“余大少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的表少爷昨日的话何等无耻?但凡上头有祖宗,知道自家来自哪里,昨天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你说能让他不仅这么想了,还大庭广众说出来是什么缘故?”余嘉鸿用带着深意的口气说,“安顺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立场。”
上辈子星洲沦陷,郑雄成了帮日本人的伥鬼,害得好几家华商灭门,安顺一直良心难安,恨自己明明猜到了郑雄在干什么,却不去查证,如果……没有如果。
这辈子郑雄的事已经有了定论,郑安顺也不会再被愧疚困扰。
郑家管家义正言辞:“这是污蔑。大少爷怎么能给郑家泼这种脏水?郑家还在为筹赈会奔波。表少爷的话怎么可能代表郑家?”
余嘉鸿不置可否地笑了一声:“但愿吧!”
叶应澜一下子明白了,余嘉鸿是想要帮郑安顺撇清跟郑家的关系。
余嘉鸿拉住叶应澜:“我们走了。”
叶应澜跟着余嘉鸿上车,这回余嘉鸿坐上了驾驶位,按了喇叭,开车离开。
他们倒是离开了,留下了已经报上家门的郑家管家,边上的看客还没散开,正在议论纷纷:
“听余大少爷的意思,郑家不支持打日本人?”
“不会吧?他们可是给筹赈会在买粮食,知道他们支持筹赈会,我一直去他们铺子买米。”
“也有可能,你们想想报纸上说的,那个陈家二少爷说的话。他们是亲眷。”
“报纸?什么报纸?”有人问。
一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衫的男人拿了一份报纸读了起来:《酒楼痛斥汉奸,共唱告别南洋》
文章先是叙述了昨天的整件事,这个穿长衫的男人还特地指出,这个被打的人,正是郑家的表少爷,陈家的二少爷。
后面说,纵然支持国内抗战是主流声音,也不乏唯利是图的那些华商,认为中国已经跟他们这些移居南洋的华人无关,也有人说出“不战亡国,战亦亡国,支持抗战实际上在增加中国人的苦难。”
文章对这群人的言论进行批驳。呼吁华人团结起来,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
“这么看来,余家大少爷说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别说是陈家二少爷了,就是郑家二少爷这么说,这不代表郑老爷是这个想法。家族大了出一两个败家子也正常。”
“未必,我们这种根本接触不到他们这群人,但是他们这群大华商大家都熟悉,余家少爷这么说,未必是无的放矢。”
“怎么可能?”郑家管家大叫起来,“我们老爷为国内筹集粮食殚精竭虑,他们这是血口喷人。”
“郑家粮铺价格是便宜,但是用几年的陈粮掺在新米里,当新米卖。还有他们的米粮一直是散装的比袋装的贵一点是为什么?还不是他们袋装的是连着布袋的总价吗?”
“对啊!郑家粮行的东西,真不怎么样?”
“你想要好东西,就要出贵价。”
“……”
话题已经偏了,郑家管家不再理论,他转头去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翻看那条新闻。
昨天晚上陈家老爷和陈家太太带着被打得鼻青眼肿的陈二上门来讨要说法。
陈二虽然排行老二,但是上头的老大早年夭折,陈二是陈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
被郑安顺这个贱种打,陈家夫妻怒火滔天。
奈何当老爷听说郑安顺有余家大公子撑腰之后,不痛不痒地说了句:“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我们跟余家相差悬殊,就说老二说话不看场合,外头都在救亡游行,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没被打死算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