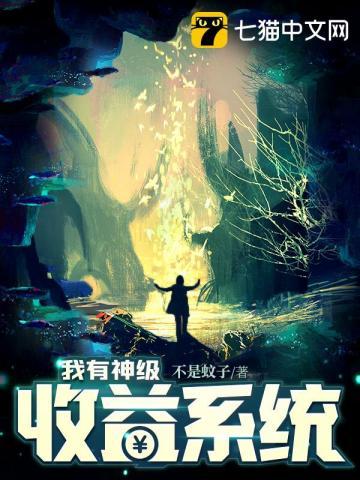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踏莎行贺铸 > 何患无妻(第2页)
何患无妻(第2页)
现在虽然没人认出她,但不保证日后不会。而且这个亲信的身份根本经不起推敲,如今入仕也讲究仪容,一个面有麻子的人就不太可能被陈籍收入麾下做事,若真是破格收了,必是有大才,想来再低调,也应该有人知晓,但若是赖清泉多方打听,也打听不出她这个人,岂不奇怪?
“嗯,钟为盏账下的人我自会处理,今日见过你的你也不必担心。”陈籍的桃花眼微微一狭,“你如此担心战局,不如留下来当个幕僚,尽一尽心力?”
什么叫“都会处理”?赖清泉这种人物是好处理的吗?赖家也是历了两朝的老人了,处事也霸道,族里人在兰考县做官,还把政绩立到别人地界儿上,当初她回老家兴仁府时曾路过赖公泉,见微知著,自然知道赖家不是好相与的。
虽然今日仔细说来,她也算在鬼门关边儿上转了一圈,但陈籍那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了,会为这事冲冠一怒?自己也不是他的红颜,他也犯不着如此。
陈籍见她一脸不可置信,也觉得有些好笑,道:“顽笑而已,我派人送你回去。”
明新微狐疑地打量一下他,什么时候古板伪君子也会同她顽笑了?
“不用。让明二哥安排就行。”
她才不愿让陈籍的人监视一路呢,况且,若有机会,她还想去若元寺一趟呢……不知道呆云豹现在在做什么呢?
陈籍见她不知想到什么,神色忽然一柔,他风月场上见多识广,哪里看不出这是小女儿情态,又见她一力推拒自己派人相送,难道是想半路同人幽会不成?罢了,这种女子他回去后就会退婚,且看她自作自受,自食恶果,他陈籍何患无妻?
他压下胸中气闷,皱眉道:“明二此人成事不足,先前接你就出了纰漏,不然你怎么会陷入今天这种险境?”
明新微不乐意他对明二哥指指点点,反驳道:“不关他的事,是我走到半路……算了,懒得和你多说,你就少管……”
“走到半路怎么?”陈籍蓦地打断,“忽然发现舍不得你的姘头,要和人淫。奔?”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没头没脑发的什么疯?”明新微脸色也难看起来,“既然陈官人上次帮我传了信,那我以为我们就是盟友关系了,此次我冒死来此送上诸多情报,陈官人没有半句感谢也就罢了,反而对我指手画脚,是何道理?”
陈籍见她话里话外,全然没有反驳自辩的意思,只怕当真动过和人私奔的念头,只觉得如鲠在喉,脸皮被人扔在地上踩。要知聘为妻,奔为妾,这人放着他陈籍的正头娘子不当,竟要与个贼寇无媒苟合,简直可笑!
明新微见他一副比自己气得还厉害的样子,反而笑了:“我记得上次同陈官人说过退婚的事宜,陈官人当时也没有异议,难道……”
“大丈夫何患无妻?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陈籍截断她的话头,冷笑一声,面色铁青地转身走了。
人虽气走了,但好歹没有忘了正事,让人传了明二哥过来,兄妹俩见面,抱头哭了一阵,自有一番离情来叙。明新微交代了自己的一应始末,又问明二哥福云等人可好,知晓都已回了兴仁府,内心稍安。
“要我说,你也今日动身,趁早回了兴仁府,不然我这心里总也不安定。”明二哥道。
明新微自有打算:“我打算回东京去。”
明二哥问:“为何?”
自然是因为庞秀,如果有机会,自然要去东京面见太后。但这话不能说,明新微就道:“嗯……此次一番惊吓,离家久了,分外思念爹爹阿娘,也累得他们挂心,自要回去告罪安慰一二。”
“在理,在理。”明二哥点点头,“也好,此处往东京的路,克恒再熟悉不过了,这次由他派人护送,保管出不了差错。”
“何必劳烦外人?写信叫几个家丁健仆护送便是。”
明二哥把头摇的拨浪鼓一般:“莫说几个家丁,就算我不在役上,陪你走一遭,心里也是打鼓!克恒手下办事的石谨,我也知晓,武艺高强,为人审慎,不比家丁好用?”
这话半真半假,她想,多半陈籍同明二哥打过招呼,算了,还怕他不成。
启程之前,陈籍没再出现,派过来的石谨确实是个魁梧的好汉。身高五尺九寸,气宇轩昂,据说早年曾梦想去皇城司当亲从官,为天子守大门,但由于筛选标准为身高五尺九寸一分六厘,就是这一分六厘之差,被刷了下来,后被陈籍收拢到手下做事。
这段轶事被明二哥说给明新微听,一是想表示石谨武艺出众,可堪拱卫皇城,二是想表示陈克恒慧眼识珠,知人善任,君子大才,可为良配云云。
明新微听了,心里也琢磨出两点来。
其一,这石谨是个毫无背景的榆木脑袋。一分六厘有多少呢?你把五尺九寸一分六厘和五尺九寸的两个大汉并排放在一起,保管你看不出差别来。在人精扎堆的皇城,老实人不知变通,被这点子条条框框限制住,再常见也没有了。但这石谨的武艺又应当很是不错,不然全然可以用其他理由剔除他。
其二,陈籍很会用人。不但能捡皇城司的漏,还能专门选中这种一板一眼的老实人来护送她,她都能猜到,陈籍只须稍加提点,石谨必然奉为圭臬,不论她如何舌灿莲花,就算说破了天去,恐怕也不会任她稍离路线一步。
果然,自上路以来,这位石谨大哥就把嘴巴闭得像蚌壳一样死紧,明新微只要一打起帘子,还未开口,他便一脸惊恐地打马疾行,等她讪讪放下帘子,他才送了一口气似的又打马回还。
等到这日晚间,众人投宿邸店,明新微才找着机会,在马厩里截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