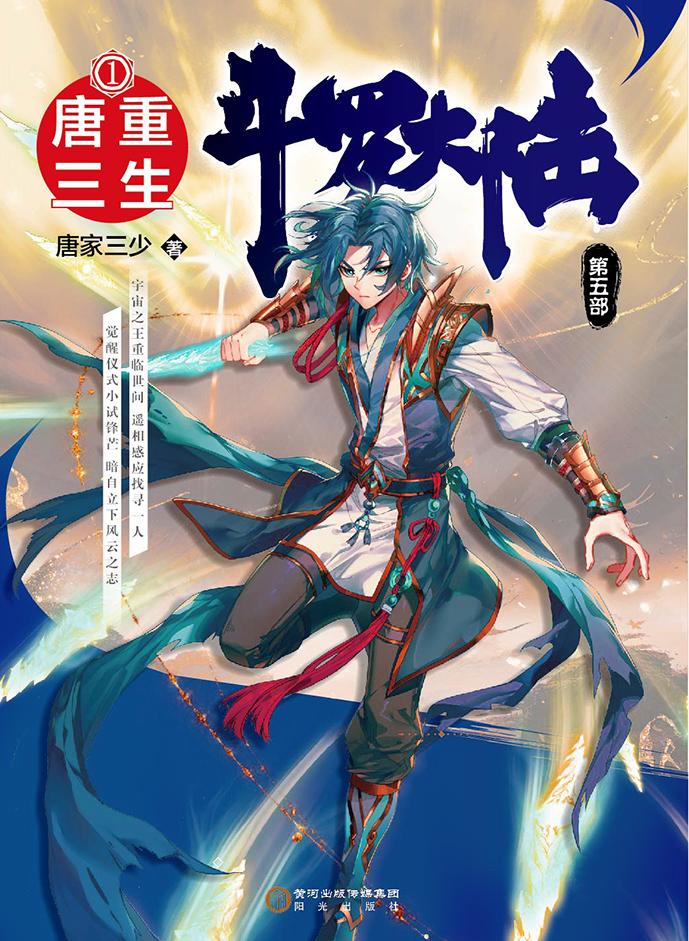秃鹫小说>鱼目混珠是指什么生肖 > 第4章(第2页)
第4章(第2页)
傅至景作讶异状,“怎么是你?”
孟渔磕巴道:“我、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病患不领他的情,别过眼留给他一个冷冰冰的侧脸,“我记着你这两日斗蛐蛐斗得正开心,既已与我断交,不必如此客气,免得扫了你的兴。”
孟渔急切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榻旁,我了半天说不出下一句。
“你什么?”傅至景反问,“不是你说的与我再不往来,不是你自己挪了位与我分桌?”
确实都是他所为,孟渔哑口无言。
傅至景眉眼冷峭,薄唇翕动,“你走吧。”
孟渔被劈头盖脸地刺了一通,又实在嘴笨,连病中的傅至景都说不过,心里盘算着等对方病好了再赔礼道歉,咬唇道:“那我先……”
傅至景没想到孟渔真敢走,厉声,“你今日出了这个门,往后就再也不要进来。”
孟渔愣住,到底要不要他走?
他犹犹豫豫地往前靠近一步,见傅至景没阻拦,心里高兴,那就是要他留下来了?
他整个人都松快了,一个箭步坐到了塌上,端起药碗,“我喂你。”
傅至景睨他一眼,“谁要你喂?”
话是这么说,却张嘴喝下了递到唇边的药汁,苦涩顺着舌尖一路蔓延到喉底,勉强喝了几勺,自己端过碗底一口闷下。
孟渔见他把药喝完,长吁一口气,嗫嚅着说:“我样样都比不过你,人人都向着你,其实我只是有些羡慕……”
也许还杂糅了一点点的嫉妒与不甘心。
傅至景盯着近在眼前的秀气面颊低声问:“麦芽糖好吃吗?”
好突兀的发问,孟渔实诚地点点头。
傅至景抓住他的手,往摊开的掌心放了块用油纸包裹住的甜点,问他:“比奶酥还好吃?”
孟渔愣了愣,三两下将油纸打开,露出里头方方正正乳白色的奶酥,双眼放光,想了想笑道:“都好吃。”
“不成。”傅至景蹙眉,“你只能选一个。”
孟渔眨眨眼,似乎隐约触摸到对方这句话底下更深沉的含义,在傅至景强势的语气里做了抉择,小声说:“奶酥好吃。”
傅至景的脸上这才有了点浅薄的笑意,让他把奶酥裹好,将他拽到榻上,“陪我躺会。”
孟渔脱了鞋挤到塌上去,手脚都挨着傅至景,很快就捂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翻身跟傅至景面对面,嘀咕着热,想坐起来,被傅至景摁着动弹不得。
“心静自然凉。”
说话间离得太近,呼吸都扑洒到彼此的面颊,孟渔一睁眼就能见到傅至景清冷的五官,长而直的睫毛如同乌黑的鸦羽,眼波明,唇峰利,恰如人间雪泉上冰,凌凌透着一股别样的清艳。
他倏地不敢再看,背脊也蒸出阵阵热意。
等他热得迷迷糊糊睡过去,朦胧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扫过他的脸颊和唇瓣,又在他将醒不醒时像捉摸不透的鬼魅般迅速远离。
他想起去年偶然撞见同窗们课后聚在一起嬉笑,好奇地围过去,听得拉长的一句“粉香汗湿瑶琴转,春逗酥融绵雨膏”,纵是才疏学浅的孟渔也能听出那不是什么好诗,可双腿却挪不动道,将下一句也听了个真真切切。
“浴罢檀郎扪弄处,灵华凉沁紫葡萄……”
不知谁往他手里塞了张画,挤眉弄眼地跟他说是好东西。
孟渔打开来瞧,只见纸上画着两个交缠的小人,姿态亲密无间,羞刹不知风月的少年人。
他慌慌张张把画还给同窗,转过身却猛地见到傅至景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从头到脚噌的一下滚烫,好半天都没敢跟傅至景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