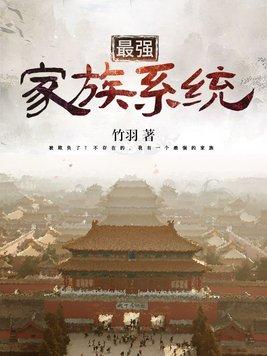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古代的科举考场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采纳裴陡行的法子,和他们的诉求并不冲突。
然而——
江两鬓转头看向裴陡行:“你想针对的,其实只有李蓬蒿吧。”
闻言,裴陡行微感惊愕,面上不动声色,并不作答,但江两鬓清晰地捕捉到他眼底的寒芒乍放。
“诸位御史,你们可得好好查啊。”他轻咬牙关道。
三个回廊、两个小院过后,就到了礼部贡院往来迎送的中堂。
江两鬓几步跨到,轻一扣门,报:“御史台察院三位监察御史已带到。”
屋内传来回话,是窦尧本人的声语:“进。”
吱呀一声,门开;趋步向前,穿门而入。
一进去,被白昼似的灯烛当头一耀,迎面见到这样一排人:为首一个老头,披头散发、赤足裸膊,穿一件肥大的袍子,衣襟还大开,好似对竹林七贤的丑仿;第二个是个侏儒,手伸进裤裆里去掏,好像在抓痒,抓完了还将手放到鼻子下嗅,感慨自己的阳刚之味;第三看似正常,却一直捂巾帕咳嗽,料来身有肺疾;第四个起初坐着还是个高大威猛的好样子,站起来走两步,立时就叫人扼腕叹息——是个瘸的。
第五个,黑,黑得铛亮,活似个昆仑奴;第六个却反了过来,白得跟纸似的,且眉眼柔媚,颇有狐貍之态;第七个正啃着东西,不是肉不是菜,竟是那刚削下的桑树皮,吭噌吭噌咬一片,嚼几下就吞了下去,直呼美味;他是个胖子,胖却矮,在他旁边那个,则是高而瘦,简直嶙峋,像一根竹竿挑着一身衣服,手上有个团扇,扇书“镜中别墅”四字。
八个人,当真是老弱病残、黑白胖瘦。
八个人,正是江两鬓从考场上依靠笔迹鉴定推断出的八个嫌疑犯。
“诸位御史深夜来访,辛苦辛苦!”窦尧的声音再度传来。
“我知诸位定是忧心适才科场那把火,才忡忡赶到;我也一样,火一起,我就担心有诈,火灭了,我便着手探查,果不其然,让我查出有这么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欸!趁着科场火动乱期间,交相传义、勾结舞弊!那火就是掩人耳目,幸得我等发现得早啊!不然这大唐选举良才的问缨之地,倒成了他们兴风作浪的所在!”
微一停顿,最后结话:
“现今,那趁乱舞弊的八人,我都纠集在此处,诸位御史,你们——”
“尽管调查。”
宫苑御史问讯秘笈
奇形怪状的八个人。老的丑仿竹林七贤,弱的幼童一般体量,病的两个肺要咳出血来,残的有半条裤管都是空的;后面黑白胖瘦也各有姿态,但一样的懵、痴、乖、凛,白日走到街上都使人森然。
八个嫌犯,就这样站在江两鬓一行人面前。
先前的推断全数坍塌。窦尧没有阻止他们调查,还把人亲自送到他们面前!
江、熊等人犹在愣神之际,后面跟随的裴陡行先沉不住气了,几个箭步挺身前来,目光眈眈直视窦尧道:“泰——窦,窦主司,怎么就这八人?我也举报了人的不是?那李蓬蒿和权鹤一,他们私通勾结、传递韵书,也该叫过来,窦公你看,是否是这个理?”
那窦尧正端坐在席,手上捏个朱砂沁玉器在把玩,本自笑吟吟,见到裴陡行进来,整个面堂霎时间里黑下。
这副神态一出,裴陡行登时就吓住,下唇一个哆嗦发起白来,颤巍着回过头,去看江两鬓后面立着的三位御史,指望他们说点什么——然而八位嫌犯俱在跟前,先前那三句说辞也便没了出口的必要,熊浣纱等人于是都是木木的,只语不发。
见此情状,裴陡行顿时急得满头大汗:想把家父裴延龄搬出,苦于屋子那头立着八个外人,无法光明声张;想凑过去耳语,见窦尧那森严的派头,魂都丢没了,哪还有动口舌的气力。
正自焦心,忽就听窦尧悠悠说道:“我有说没叫他们么?”话音未落,又听屋子另一首紧跟着抢上来一句:“裴郎真是念我们念得紧啊。”倏然回首,正是李蓬蒿和权鹤一款款行来。
两人来到立定,面上俱是笑意。权鹤一多是挑衅,站好了,手上还要动作,比作刀状,在脖颈间一划,做杀人封喉的示意,自以为有模有样,实在是像极了稚气未脱的顽性少年。
旁边的李蓬蒿倒好些,一直都是温吞如水的一对眼,只是电光火石间错了一错,与江两鬓暗自交了个眼神,两人心领神会,都凛起色来,预备应对接下来的事变。
见到这两人出现,裴陡行脸色微有松动,勉强牵起嘴角,不尴不尬地笑了一下,道:“来了是吧。”尾音未落,身子已回转过去,向着三位御史道:“就是他们,私传韵书,一个李蓬蒿,父亲是滁州刺史,一个权鹤一,家世不用我说诸位想必清楚——多出来的《切韵》,就在这李蓬蒿袖子里,御史们,你们尽管查,我亲眼看见的!”
他这边刚讲完,那边窦尧便高声喝道:“没大没小!你大人教你的礼数哪里去了?!三位御史犹未落座,未交流职称名讳,你小子在这里叫喊些什么?命令谁呢?!”
这一喝,登时像一鞭子抽在裴陡行的后脊梁上,他一哆嗦,作受惊的猫状连连后退,嘴上要道歉,一出口就支吾了,呜呜囔囔一串音,直退到屋子西首的厅壁记前才堪堪站稳。
整治完这一头,窦尧将目光转过,望向熊浣纱等人,眉开眼笑道:“诸位御史,未请教尊姓大名。”
语言前锋林羌笛率先应话:“御史台察院监察御史越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