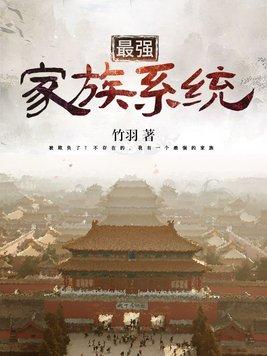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野狗梁川 诗无茶简介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我脱口问道:“你爸妈呢?”这次是没有尽头的沉默。我没过多追问,让他期末考试这一个周去我家住,他答应了,当晚同我一起回了家。家里所有的备用钥匙在保姆那里,我向肖禾指了指保姆房的位置,告诉他有什么需要就去敲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妈出差,我吃了宵夜便回屋早早睡下,肖禾一个人留在客厅复习。半夜醒过来时肖禾还没回房睡觉,那时已是凌晨,我放心不下,决定出去看看,结果客厅漆黑一片,空无一人。我不想吵醒保姆,于是开了灯,打算挨个挨个打开房间门查看一下。刚刚走到第二间空房门前,肖禾的声音遥遥从某个地方传来。我寻着声音找去,发现他站在客厅外的小花园里,穿着一身白色的睡衣,不知是月色太过凄清还是他本身就很单薄,脸色看起来竟是苍白得泛了点青,即便他就笑着站在那里,也让人感觉摇摇欲坠。我走出去,肖禾站的那块草地正对着我妈房间的窗户,窗帘没关,我往里看了一眼,往常一丝不苟的桌面今天有些杂乱。我当时要是再多看几眼,仔细看看,会提前发现插在我妈电脑上的那个u盘,可惜我没有。我的注意力被肖禾踩在草丛里的光脚吸引去了,前一晚才下了雨,草泥上的雨水都还没来得及干。我皱着眉头把他拉走,嗔怪道:“院子门口放了换的拖鞋,就算没看到也不要打光脚。”他还是那样笑笑,好像一笑什么事都可以不计较,他自己不计较,也替我赊了一场不计较。考试结束那个下午我和他站在教室外的阳台上晒太阳,他突然问我毕业于哪个小学。我说了自己小学的名字,他若有所思地问我,眼里甚至带着点羡慕:“是个很不错的小学吧?听说是贵族学校。”我对这个称呼有些嗤之以鼻,什么时候贵不贵族是靠钱来划分的了,麻雀插上凤凰毛也还是麻雀,张嘴叫一声就原形毕露。我随口问道:“你想去看看?”“能进吗?”“能。”我有些打瞌睡,闭着眼睛胡说,“早放假了。随便说个什么身份就能进。”然后我们翻墙进了去。肖禾闹着要去我原本读书的班上看看,我轻飘飘拖着步子带他去了。门窗当然是紧闭着的,不过到了那里他似乎对教室内的风景不感兴趣。那天傍晚暮色极好,他迎着天光,问我:“夏泽,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姓肖的管家?”我愣了一秒,硬生生把那个人从回忆的泥沼里拖出来,想着他好像是姓肖。“是啊。”“他有给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吗?”“他给我说过的话很多。”时隔两年,他的音容在我这里早已发灰了,可被肖禾这么一问,许多画面似乎又鲜活起来。“他有没有说过他爱你。”“说过。”当年这三个字他说出口时带着濒死的绝望和平静。“他是我爸。”“是吗。”我感觉这一瞬间我与肖禾的距离被拉到了初识以前,甚至更远。或许是那时我的脸色和语气都冷到了极致,肖禾忍不住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我确实也是这样,我巴不得自己周身都冷下来,冷到足够让我的思绪在这一刻冻结,不去深想和回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叫肖禾的朋友,从一开始就带着怎么样的目的步步为营地接近我,那些对我异于常人的温和与包容,和我谈天说地时共享的愉悦,心甘情愿为我受的伤,全都是一层层的伪装。“他从哪里跳下去的?”他一寸一寸地踱步,“这里吗?还是这里?”肖禾走到栏杆边上时我下意识看了他一眼,就是那一眼,让他找到了答案。“看来是这里。”他定住了,站在那里透过我回忆到了什么美好的事情一般,眼神犹如春风拂水那样荡漾,“夏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长得有些相像。”“我爸有病,”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有些苦笑着摇头,“我妈发现他不对劲的时候抱着我大哭了一场,第二天就自杀了,那时候我才七岁。后来他就走了,很少联系我。他以为我不知道,他躲在哪些地方偷偷看我,我一清二楚。”肖禾朝落日的方向仰头深深吸了口气,很大一口,嘴角慢慢化开一个弧度,是那种要与这个世界后会无期的弧度。“你像我,但不是我。”他说,“所以他爱你。”我没拉住。残阳下的楼底开了一朵红白相间的花。我痴坐在楼上,透过栏杆的缝隙看着那朵花,直到天黑,直到家里人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在这里找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