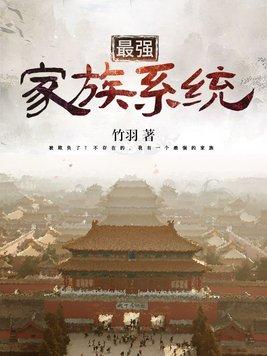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野狗梁川介绍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每次他一靠近他妈,他妈就瞪他:“小杂种!又要干嘛?”他不想惹他妈不高兴,所以他从来不敢跟他妈说话。久而久之,他好像就不会说话了。他敢跟他妈说话那年他六岁。起因是六岁生日那天,他从一大早就期待着他妈回家,可他妈一般要晚上才见得到人。他觉得一年到头就这一天最难熬。那时电视机里的小人儿对着另一个小人儿说:“那么羡慕,为什么不自己出去看看?”他直勾勾盯着屏幕,心想,对啊,我为什么不出去看看?他趁他妈出门聚会的时候逃了。那是他第一次呼吸到那所八十平房子以外的新鲜空气,蓝天碧树,花鸟鱼虫,六岁的他像新生儿一样在这个世界初来乍到。他不知疲倦地在这所城市走马观花,逛了好久,他突然想,会不会也有人在电视外面看着我?他不能被看到,他怕他妈发现他出门。于是他慌不择路地找地方藏起来,最近的东西是那棵巨大的行道树,他跟着电视里看过的,手脚并用爬到最茂密处。他像只兔子一样缩着脖子提心吊胆地坚守阵地,在那棵树上维持着一个姿势一蹲就是半天。背后突然响起的动静让他吓得差点掉下去。他惊惶转身,才发现动静来自下面的院子。院子里站了一个人,跟他差不多大,即便一个人待着,也神色傲傲的。他看见那个人的第一眼就知道,合该人人都长得跟电视里一样好看,他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人。他看见那个人提着一个蛋糕坐在自己身下的椅子上,原来电视里闻不到气味的蛋糕是那么香甜,他一天没吃东西,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慢慢朝下面滑了很长距离。四目相对那一刹那他心想,哦,原来那个人鼻尖上还长了颗痣,好看的人连痣都长得那么好看。他要是有那么好看,他妈会不会多喜欢他一点?他记得电视剧里这种情节的下一秒,那个人就该尖叫了。然后他会被抓起来,被审问,再被他妈领回去。结果那个人只是看着他问:“你要不要吃蛋糕?”他觉得此刻自己应该说什么,“好的,谢谢”或者“不用,谢谢”。他试图张嘴,舌头顶着上颚,一个字也说不出口。等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缺乏说话这项技能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理他,把头转回去了。他慢吞吞地跳下树,怯怯地站在院子里,不敢过去。结果那个人过来牵他。糟糕,应该把手擦擦的。他心想。那个人的手真软啊,他被牵着,觉得自己和那个人像电视剧里的青梅竹马。他在桌边坐下,看见对方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xx附属小学,一年级(二)班,夏泽。夏泽,夏泽。他在心里默念,这名字真好听。夏泽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摇摇头,没有名字。“那你叫默吧。阿默,沉默的默。”阿默,阿默。他又在心里默念,我有名字了,我叫阿默。可是他看见电视里取名字的都是父母,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抱着取了名字。他还没有问过他妈,她给他取了什么。万一他早就有名字了呢?他得回家问他妈。翻墙逃走前他看着阿默进去的那个房间,在心里说,你请我吃蛋糕,下次见面,我回赠你一束向日葵。这次他妈回来得意外地早。当他在家楼道里看见连鞋都慌忙跑掉一只,正准备出门报警的他妈时,便做好了挨一顿打的准备。没想到他妈冲过来抱着他,脸上哭得妆不是妆泪不是泪,不顾楼道里闻言纷纷出来看戏的邻居那些怪异目光,扯着嗓子号哭道:“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们找到你了……他们找到你了……”六岁的生日过了一半,他连夜搬了家。后来他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会几句话。一是“妈”,二是“夏泽”,三是“阿默”,还有一句是问自己的名字。记忆中他第一次开口叫妈的时候那个女人刚从一场酩酊中醒过来不久,脸上带着前一晚还没来得及卸下的妆,凝在睫毛上的一层膏体已经在眼下晕成一副水墨画,整个人对着饭桌上昨晚给他带回来的夜宵胡吃海塞。夜宵是他吃剩的。此刻他妈也不管那些油腻发冷的剩菜吃进去是什么口感,抓住就往嘴里送,吃相难看,半丝在外的优雅也无。她突然就听见梁川开口叫她一声“妈”。他妈所有的动作倏然停下,手还保持着把饭菜放进嘴里的动作,那些咀嚼了一半的实物此刻在口中变成了分辨不出原料的残渣,附在她半张的口腔里,过了很久才被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