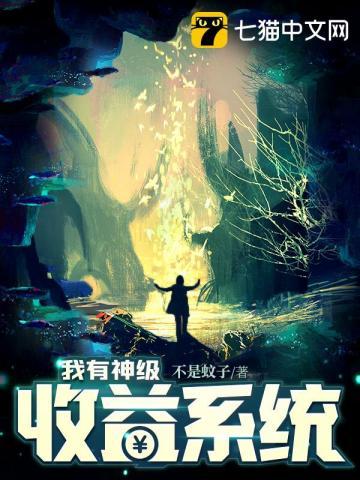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侯爷万福番外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姜弦眼睛里像是铺了一层浅薄的雾气,眼尾氤开绮色,像是受了委屈。“你弄疼我了。”她抱怨。陈淮睨了一眼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落下的薄毯,又十分君子的把垂开一个大领口的中衣提了提。他抱起姜弦,不紧不慢叹了口气:“这可怎么才好?”“什么?”姜弦不由自主问。陈淮道:“我可不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在姜弦还在想这句话似曾相识时,陈淮已经贴近了她耳边。温热的气息拨过她耳垂:“刚刚在交颈泉,我想的净是旖旎。”薄薄的中衣压不住陈淮身体的温度,正如未经人事的姜弦挡不住突然灌进脑海里来自嬷嬷们详细的讲解。她有些害羞地蜷了蜷腿,殊不知却将自己更贴合的送给了陈淮。等沉沉的大门开启再合上时,她就只能看得到陈淮了。这可怎么才好?姜弦满脑子全是陈淮调侃的这一句。眼前是一个二十四岁、常年在军营、兴许还是听着荤段子长大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姜弦眨巴着眼睛,贴着陈淮的胸膛,紧紧攥着陈淮的衣裳。她试探着掀起眼帘,正对上陈淮的眼睛——与刚刚截然不同,此时盛满温情。陈淮带着薄茧的指尖轻轻撩开跌落在她眼前的碎发:“怕?”怕吗?姜弦的心微微收紧,她清晰的知道,不是怕,说不清楚,有些奇异的隐秘。这种暗伏着的情绪像是刺激着她的神经,让她认不住耸耸肩。那模样……陈淮俯下了身。他轻抚着姜弦的脸颊,正如同姜弦勾绕着他的脖子。二人相抵相缠,卷着铺散在圆床上的纱织红绸,跌落起伏。姜弦被激起战栗似的轻吟,她紧紧抓着陈淮的背脊。那里的疤痕像是带着沙砾感的陶壶,让她一瞬间清醒。“侯爷?”陈淮一停,疑惑地看着姜弦。“这些疤……”陈淮看着姜弦的指尖游走,像是要一点一点把它们抚平似的。他攥着姜弦细弱的手腕,压回到头顶,二人鼻尖相抵,气息相缠。他声音沉哑,携着压抑:“张嘴。”……红浪掀翻,薄绸撕裂。树欲静而风不止,水欲宁而流不停。这样不知过了多久,但姜弦在第一眼睁开时,就知道自己平日里晨昏定省养成的习惯,怕是作废了。她慢慢翻了个身,手一耷拉,便碰到丝滑的红锦。一时间昨夜的放纵便如同风卷浪起,破破碎碎、零零乱乱一股脑涌了进来。她揉了揉眉心,半晌才叫了一声鹤云。鹤云进殿后,先是一怔。旋即小心将姜弦扶了起来。她利落地挂起帷幔,又把一切都收拾妥帖,才又走到姜弦身边。“几时了,鹤云。”鹤云道:“夫人放心,平日您起的早,今日也没太晚。”姜弦放下心来,“侯爷呢?”鹤云歪头想了一下,奇怪,似乎自昨日侯爷要了水,为夫人按了按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她皱着眉,摇摇头。姜弦没说什么,只是让鹤云梳妆。鹤云将檀木梳子轻轻卡在姜弦的发间,为她盘了发,又挑了几只上眼的簪子,才将云鬓挽好。等做完这些,鹤云便低过头去看姜弦,她似乎还是躲不开乏,微微合上了眼睛。鹤云无法,只好按着自己的想法为姜弦上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日而给鹤云平白给了暗示,她总觉得姜弦很不一样,就像是开在山野里的野茶花突然被精心浇灌,霎时间饱满充盈、鲜艳欲滴。这样好看的夫人,别说侯爷,就连她一个姑娘家也觉得就该好好娇养着……鹤云静静站了一会儿,直到姜弦垂下头把自己迷迷糊糊晃醒,才出声道:“夫人要吃点什么。”姜弦又问了句时间。鹤云道:“辰时未过。”姜弦停了一下,这离陈淮平日练剑已经过去很久了。她道:“还是先去找侯爷。”鹤云本来想告诉姜弦陈淮昨日就已经吩咐下去了,要夫人顾及好自己,万事随心,不用管他。不过,既然夫人想和侯爷在一起,那她劝什么劲。姜弦道:“你煮平日的粥,备一些点心就好。”说罢,姜弦自己慢慢走了出去。昨日烙印似的印在她心里的萤石和鱼尾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悄然取了下去。这自是应该。凤华山庄是陈淮求来成婚的场地,等三日已过,他们便要回去了,自然没必要平添麻烦。姜弦所求本来不多,这些已经足够,自然没什么遗憾。她转眸对身旁跟着她的侍女道:“烦请你们待会儿把后殿收拾干净,物归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