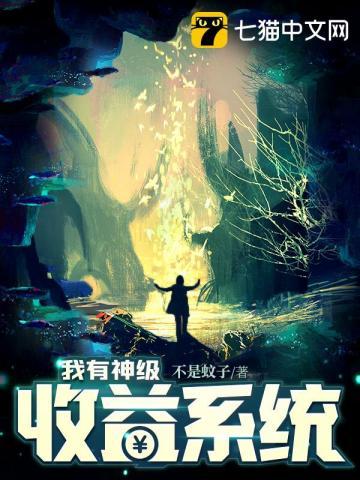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白日梦是什么意思 > 第16章(第1页)
第16章(第1页)
谭一鸣家里有车来接,他爸妈忙生意,就请了个司机来接他上下学,这会儿贺庭远就坐在谭一鸣家的车子里,整个人木愣愣的,感觉特别不真实。
"你也真能忍,自己不难受吗?"谭一鸣说着,又摸了摸他的额头,"这也太烫了,你烧多少天了?可别烧出肺炎来了。"
贺庭远往后缩了缩,下意识要躲开他的触碰,可又隐隐有些期待,于是就僵直地坐着不知所措。
谭一鸣收回手,又催着司机开快些,然后翻出一瓶水来,拧开瓶盖递给对面:"你先喝点水,降降火。"
贺庭远看看那瓶水,视线又上移到那只递过来的手上,这只手他在篮球场上看了无数回,修长有力,筋骨分明,运球投篮的时候动起来尤其性感,而此刻这只手就握着一瓶水,朝自己伸过来,贺庭远看着那上头圆润干净的指甲,就觉得心口砰砰乱跳,再也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来。
他乖乖把水接过来,又乖乖喝了一口。
"多喝点儿呀,生病要多喝水。"
贺庭远抬着眼皮瞅了他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睛,咕嘟咕嘟喝了大半瓶。
他们城市也不大,没多会儿就到了医院门口,贺庭远就一路跟着谭一鸣折腾,也不用他开口说什么,就被谭一鸣领着七扭八拐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了躺椅上,手背利落地被扎了一针。
谭一鸣也没歇下来,又跑去给他买了些药,最后提了一袋子东西回来,总算松了口气,并排坐在了他边儿上。
"你差点就烧出事儿了,还好我带你来医院,"谭一鸣又是担心又是无奈,"钱可不是这么省的,你要是身子出问题了,有多少钱都没用啊。"
贺庭远默默看他忙活了半天,这会儿忽然就忍不住,稍稍抬起手,给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谭一鸣一愣,看到他指尖的汗渍,又咧着嘴笑了:"你看你是不是让人不省心,折腾我一身汗。"
贺庭远觉得这话有点不好理解,理解歪了怪让人害臊的,于是就唔了一声,垂着脑袋认错:"我以为不严重的……对不起,让你费心了。"
谭一鸣忽然就有点语塞,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觉得这个模样的贺庭远有种莫名的乖巧感,说起来他和这家伙来往的次数不多,可每次都觉得这人看起来好像很闷,但哪里又软软的,好像戳一下还会往后缩,小仓鼠似的,想想还有点可爱。
"反正你照顾好自己,以后可别瞎对付了,"谭一鸣侧靠在椅背上,歪歪头,笑着逗他,"你不来上课,我就没饭吃了,所以你得养好身子喂饱我,不能始乱终弃。"
贺庭远:"……"
真的不怪他多想,这人说话实在是太不着调了。
"对了,学校要抓仪容仪表了,昨天老师说的,下周一就开始检查了,你记得去把你这头发剪了,"谭一鸣忍不住拽了他一绺儿头发,憋着笑说,"你这跟金毛狮王似的,刘海儿留这么长,眼睛都挡住了,你能看清路吗?"
贺庭远觉得再这么下去,自己真的要烧到五十度,于是赶紧往后缩回去,避免这人继续动手动脚。谭一鸣倒是没在意,也跟着往后一靠,随口说:"我周五也去剪个头发,有家店剪得可好了,你要不要一起去?你这头发真的得剪剪,太杀马特了。"
贺庭远从刘海儿缝隙里瞅瞅谭一鸣的表情,这话看起来好像是认真的。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嗯?什么?"
"剪头发……"
"可以啊,周五放学我就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带你一块儿?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得剪剪……"
谭一鸣又开始自顾自叨叨起来,贺庭远听着他在耳边念经,虽然都是吐槽自己乱糟糟的发型,可还是听得心里暖乎乎的。他忍不住想笑,可又不敢让谭一鸣看见,就只能努力抿着嘴巴憋住,那模样看起来有点滑稽,不过都被他杂草一样的头发挡住了七七八八,谭一鸣也没注意到就是了。
于是接下来两天放学,谭一鸣都把他送到医院楼下才走,这吊瓶正好要打三天,谭一鸣买的那些药效果又特别好,到了周五的时候,贺庭远的病就彻底好了,人也总算精神了不少。
贺庭远其实挺忐忑的,生怕谭一鸣把"一起剪头发"的约定给忘了,可又不好意思去提醒他,一整天都如坐针毡。放学的铃声刚刚打响,他就竖着耳朵听身后的动静,隐约听到谭一鸣在和其他人说话,笑哈哈地扯淡了好半天,他越听越失望,觉着那家伙八成是忘了,于是就坐在凳子上无精打采地收拾东西。
然而还没收拾完,就听到那把熟悉的嗓音喊了一句:"贺庭远,你快点儿!收拾东西那么慢!"
贺庭远一愣,猛地回头,差点把脖子扭着。
谭一鸣旁边还站着两个男生,那俩人瞅了瞅谭一鸣,再瞅瞅贺庭远,很不甘愿似的异口同声说:"还带他啊?"
谭一鸣瞪他们一眼:"咋的?有意见?"
一男生切了一声,扁了扁嘴:"行吧,他那头发是该剪剪,拖把扣头顶也就那造型了。"
另一男生哈哈大笑,指着他鼻子笑骂:"你他妈写语文卷子咋没这造诣啊!"
三个人就在那儿嬉笑吵闹,贺庭远的心情却跟过山车似的,呼啦高兴,呼啦又郁闷,最后憋憋屈屈地把东西收拾完,背上书包,朝那三个人慢吞吞地走了过去。
还以为就我们俩呢……怎么还多了两个傻帽儿。
总之四个男生浩浩荡荡去修理脑袋毛儿,一颗头二十块钱,先前那个男生还是忍不住吐槽:"我觉得这钱就他花得值,咱们也就十几刀,他得上百刀了,平摊下来一刀就几毛钱,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