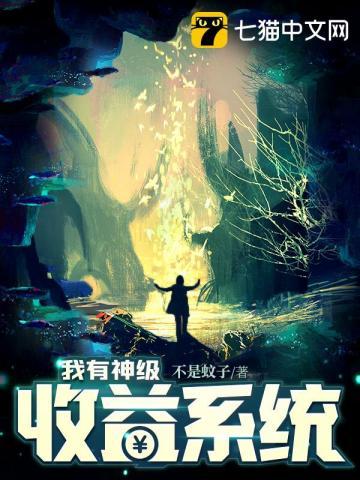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人力有时尽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共事四年,这还是聂昭第一次认同曾绍利的看法。她从旁听着,看看桌上堆积如山的案卷,一时也觉得心烦意乱。再看身边的同事,个个都是想找她询问内情却又不敢的模样,她更烦了,索性就将手里的钢笔一摔,拿起大衣出了门。
四月初的哈尔滨依旧是冬天,昨日才刚下过场小雪,与苏州河畔的桃红柳意迥然不同。只在上海待了十日不到,聂昭就已经习惯了那边的气候,有些受不住哈尔滨的寒冷与干燥了。她拢紧了大衣,沿着警局后身的甬道行下去,心中满是纷乱与忐忑——
得知聂征夷调职以后,她第一时间就去找了薛梦眉,岂知薛梦眉也是一头雾水,正坐在醉雨话婵的大堂里生气,“调职令头天晚上下来,第二天人就走了,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什么人呀这是!这哪里是调职,倒像上战场去了!”
聂昭也觉得蹊跷。
调职哪有这么个调法?不等她回来也就罢了,竟连个招呼也没跟眉姐打,更没有任何话留给她,未免太仓促了。
联想到宋方州说的,最近上海财政司诸多问题棘手,短时间内脱不开身;还有温明漱与蒋邱文,一个连早饭都没吃完就匆匆赶回公司处理事务,一个连夜南下,说是南洋商会突然被截了一船丝绸……
诸多事端赶到一处,绝不是偶然。叹只叹前些天她一心琢磨着李昆展的事,也没腾出心思关注旁的,如今想来,江浙一带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聂昭越想越怕。她不知道如何联络聂征夷,想直接去一趟南京,可刑一处又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也想过挂一个电话到上海财政司,问问宋方州是否一切安好,却又暗觉时局微妙,生怕叨扰——
这几日里,她日日守在刑一处的电话旁,却是一个宋方州的电话也没接到。以他那个性子来说,若非真忙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是怎么也忍不住不找她的。
怔茫中辗辗转转,又绕回警局门前,却见徐晓会朝她跑来,气喘吁吁地拉着她道,“昭昭——可算找着你了!新处长来了!”
“新处长?”聂昭惊讶,几疑自己听错,“昨日不还说人选没定呢么?今日怎么就突然……”
“谁知道呢!是副局长带着新处长一同过来的,刚刚过来,说这位新处长呀是从南边调过来的,看起来很是和蔼可亲……哎呀先不说了,大家都等着你呢,新处长要讲几句话,还说要合影留念!”
聂昭没应声。
什么新处长旧处长,对她来说,只有聂征夷一个处长。她打心眼儿里抵触这个人,眼下只觉心头堵得难受,似一团火烧着,索性便道,“你就说我病了,回家了,随便怎么说都成,反正我不去。”
“哎呀昭昭,你快别任性了!”
“是姐妹就帮忙,我走了。”聂昭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就走了。
兴许是刚回北方不大适应,聂昭今日有些伤风,回到住处便觉头脑发沉,往床边一倚便睡着了。
她是鲜少有梦的人,这一回却做了个梦,梦里无比真实。
那是民国五年的醉雨话婵。
倒春寒的季节里,冷雨如冰,最难将歇。少女狼狈地蜷在床上,身上裹着棉被,脸上敷着纱布,依旧不难看出唇角的红肿,脖颈处也有深深的淤青。
一声气笛响过,紧接着便是大门被推开的巨响。明黄光亮从门外洒进,那么亮,亮得少女睁不开眼睛,可仅凭脚步她也认得出来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