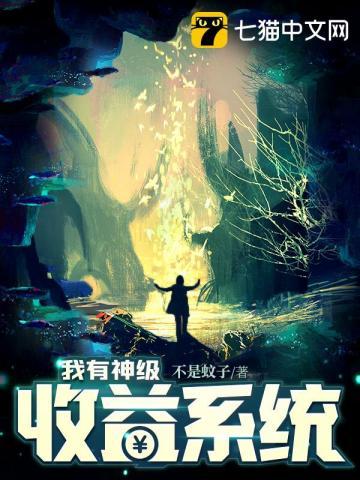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蒋小福全文阅读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佛荪吃饱了菜,这时就端着一杯酒慢慢喝着:“老董,你有话就直说。”董老爷不疾不徐地也喝了一口酒:“我是想着啊,咱们做过一次这样的买卖,多少也能估清其中的利润,这广珐琅是从南边儿来的,经了严六的手,雇人运送进京,到了咱们这里,再转手出去。这其中经手的——”他来回翻了几次手,末了伸出三根手指:“少说也有三拨人!赚得的银子,也要三拨人来分,若是中途出了什么岔子呢,别人顶多是赔了本,你我可就要得罪几位大人。这其中的关窍,老兄你看……是不是还可以琢磨琢磨呢?”他把话说得如此明白,不仅佛荪听懂了,蒋小福也立刻听懂了——他是嫌想撇开其他人,和佛荪把这桩生意霸占下来!刚想到这里,就见佛荪扭头看住了他,含着点笑。单只是看,不说话。蒋小福眼珠一转,扫了眼董老爷,对佛荪说:“要不都说董老爷是财神爷呢,这一番话跟秀才念书似的,就算听不明白,也知道是极厉害的了。”这话说得又似褒又似贬,惹得佛荪哈哈大笑起来,扭头问:“老董,蒋老板有意思吧?”董老爷笑呵呵地点头附和,心里因为知道蒋小福不是自己可以染指的了,所以无欲无求,并没有觉得有意思。倒是蒋小福,看了佛荪一眼,觉着他今日有点没来由的兴奋。董老爷的意见,自然是很有见地,可是佛荪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同意,只说要考虑考虑。董老爷不便催促,只好回家等他考虑。而这日过后,佛荪又钻进宫里,不知道忙什么去了。这两日的天开始变幻多端,时而风时而雨,好像诚心不让人外出。蒋小福蜷在屋里,守着烟枪,时而往窗外瞧上一眼,神思飘向远方,忽然想起来,当初严鹤借住到春景堂时,仿佛正是金桂飘香的秋日。不过那时候,天气尚且干燥清爽,现在却是阴了好几天,手指拂过窗户,窗棱上大概浸了秋露,有了湿润的触感。浮想中,楼下月亮门处,周麻子往外迎了出去。蒋小福一眨眼,慌忙跳下榻,也来不及穿鞋,赤着脚,咚咚咚地开始收拾屋子——最要紧的是收拾烟具。与此同时,严鹤已经进了小院,在周麻子的陪同下进入楼中。蒋小福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总是能挑佛荪不在的时候来。严鹤进屋的时候,就见蒋小福靠在榻上,抱腿坐着,膝盖抵着胸口,身穿绸衣绸裤,只露了两只白玉般的赤脚,正被蒋小福一手一只,抓在手里。保持着这个姿势,蒋小福一扭头,好像让他吓了一跳似的。严鹤一乐:“哟,蒋老板,真自在啊。”蒋小福放开手,有点脸红——天凉了,地更凉,他脚冷。脸红之余,他先发制人地问道:“你怎么老是笑我?”严鹤走过去在榻尾坐下,顺手拍了拍他的腿:“没笑你。”他这厢睁眼说白话,惹得蒋小福一蹬腿,作势要踹,但只是踹个样子:“装模作样——”刚说了一个字,他就戛然而止,连人带话一起僵住了。他那要踹不踹地一伸腿,伸到了严鹤大腿上,十分准确地踢到了某个位置。力道当然是不重,故而严鹤十分镇定,甚至还微微笑起来,只有蒋小福刷的一下红了脸,随后就被严鹤按住了腿,想要往回缩都不行!蒋小福不肯露怯,朝严鹤溜了一眼,他晃动脚掌,轻轻巧巧地又踢了一脚。这下严鹤不笑了。“蒋老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按住蒋小福的腿,他向前欠身,紧盯着蒋小福:“再说,我愿意陪你玩,你自己呢?想好了?”蒋小福立刻醒悟,知错就改:“没!”说着他趁严鹤不注意,总算缩回了腿。随着他这番动作,一个小物件儿从榻上滚下来,啪的一声落在地上。蒋小福抱着腿,伸长脖子往前看,严鹤则是直接弯腰捡了起来。这回蒋小福看清了,那是一截翠绿欲滴的烟嘴儿。这烟嘴儿不知道是何时遗落在榻上的,一直没有找着,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蒋小福一个激灵,动作抢在了头脑前面,一把就夺过烟嘴儿,握在手里。这番动作出乎严鹤的意料,他自然没有防备也没有阻拦,然而视线随之看了过去。先看着蒋小福那只手,然后向上移动,看向了蒋小福。蒋小福强自镇定,刻意笑了笑:“原来在这儿!找它好多天了。”屋里有个烟嘴儿没什么稀奇,蒋小福待客是常用的。所以严鹤挑不出错:“什么稀奇东西,值得你找它好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