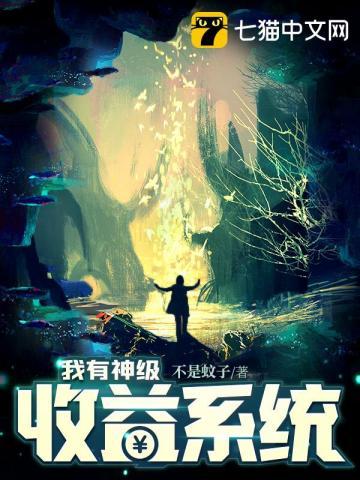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蒋小福全文阅读 > 第96章(第1页)
第96章(第1页)
蒋小福吞吐几回,周身弥漫了令人兴奋的甜腻气息,侧身撑着头看向严鹤,他慢悠悠地反驳:“我是个戏子,台上台下,都是勾三搭四的。”佛荪从刚才起,已经存了脾气,故而听了蒋小福的反驳,就不像往常那样觉得有趣:“话我是放这儿了,你有胆子就试试看。”蒋小福瞪了眼睛:“试什么?”这句话,是话顶话赶出来的,然而佛荪歪着头想了想,真就有了主意:“从今天开始,我不让你出门,你就不许走出春景堂一步。”蒋小福愣了一下,有点啼笑皆非,也有点不敢置信。他觉得佛荪太过阴晴不定,有时候像个很好懂的幼童,有时候又是个难以琢磨的魔王,而这句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另一面,佛荪说出这句话,倒是感到愉快了许多,并且发觉了养戏子的另一项乐趣,那就是给对方立规矩。他将双手放在脑后交叉了,往后一仰,躺了下去,一双脚就长长地搁在蒋小福腿上:“今儿我不走了。”余下几日,蒋小福果真没有出门。他并没有完全把那番话当真,但对于佛荪这个人,一是没有把握,二是不太敢惹,所以干脆推掉为数不多的叫局,真的不走出春景堂一步。这日早晨,佛荪看着天气好,让人搬了竹椅子放在院里,和蒋小福在院子里消磨时光。仰头靠着竹椅,他望向风轻云淡的天际,肚子上则放着一串葡萄。一只手负责捧着葡萄,另一只手负责摘下来喂进嘴里,两只腿则是脱了靴子,翘在桌上,时不时晃上一晃。悠闲地吃了半天葡萄,他一斜眼睛:“看我做什么?”蒋小福穿着月白色的绸衣绸裤,端正地坐在旁边看书,被他发现了自己偷看,索性就问出口:“你怎么不吐葡萄皮?”“麻烦。”“葡萄籽呢?”“吃了。”蒋小福蹙了下眉,对这个吃法不屑一顾,但是没言语,低下头继续看书,翻了一页,又抬头问道:“你要在这里住多久啊?”“不知道。”说完,佛荪缓缓转头,转动眼珠,看住了蒋小福。就在刚才,他忽然灵光一闪,后知后觉地怀疑蒋小福是真的不欢迎他。这时候,周麻子带着一个人从月亮门拐进来。此人年纪挺小,细手细脚,脑袋圆滚滚的,看上去仿佛是个大头的娃娃。这是佛荪手下一名小侍卫,向来跟着他办事,可以充作他私人的听差。大头听差跑步上前,顶着一脑门汗水,垂手向佛荪禀告:“货都进了崇文门了,现在正往庙里走。”“去庙里?”佛荪问:“他们的人跟着呢?”“跟着呢!董老爷让小的来知会一声儿,说稳妥起见,等过几日,再往仓库里送。”“银子给了?”“按之前说的,给了八成,余下的等仓库再验一遍货。”蒋小福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听着,不需要如何思索,他也听明白了——严鹤那方的货进了京,佛荪和董老爷已经派人接过手了,只要把这批珍贵的珐琅器藏起来,这桩生意就算做成了,至于后续如何卖出去,佛荪那边应该早有安排。大头听差交待完毕,又继续传达了另一件事:“还有,宫里来了消息,问您差事办得怎么样了。”佛荪是领了宫外的差事出来的,这时一听,立即从椅子上弹起来,顺手将手里那串葡萄往他头上一砸,顿时滚落好些零星的葡萄:“妈的!这你不早说?”说完,他手忙脚乱地穿靴整衣,二话不说就往外跑,炮仗一般冲了出去。那听差来不及解释,捂着头紧随其后,也往外跑。蒋小福先是安静地看着,直到这两人跑得没了影儿,才爆发出“哈”的一声,乐不可支了。周麻子由着蒋小福笑了一气,然后走上前道:“小老板,六爷那边传了信儿。”“嗯?”“说是要去天宁寺看古塔,问您得不得空,得空就一块儿去。”蒋小福听了,沉默许久,末了问周麻子:“你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来找我做什么?是个什么意思?”周麻子倒是不犹豫:“我要是说了,你可别生气。”蒋小福露出好奇的神色:“说。”“人嘛,做什么事情,总有个目的,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或者表面上是好的,实际是坏的,或者……”蒋小福轻轻踹了他一下:“念什么喇嘛经!”周麻子咧嘴笑了:“这可是大实话!他平白无故来找你,总要图点什么呀?”蒋小福盯着他:“我听你话里有话。”周麻子就不笑了:“小老板,我现在也看出来了,这严六爷对你是有意思,这不用我说,你肯定能看出来。可当初对你有意思的人难道少吗?这些人,现在能写条子来叫个局,也就算是好的了,要是不好的呢,像董老爷那样儿……别怪我说话难听啊,人心隔肚皮,后面藏了什么心思,谁都说不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