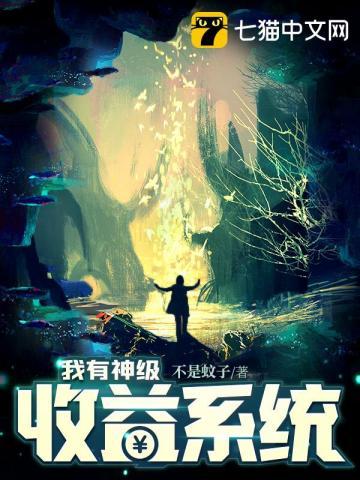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蒋小福全文阅读 > 第22章(第1页)
第22章(第1页)
在这样热烈的氛围里,王小卿的名气倒是传开来,很有些客人知晓他了。蒋小福十分得意,认为小卿果然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严二爷也很有本事,并不像老头所说的那样全靠吃瓦片。至于他蒋老板,真是慧眼识人、算无遗策。王小卿这边有了进项,春景堂的开支也富裕起来,周麻子很有技巧地替蒋小福攒了不少钱。蒋小福近日总是开心的时候多,尽管有时也会觉得心有不足,但只要不钻牛角尖,大可以快快乐乐地将日子过下去,过一日算一日。看上去皆大欢喜的局面下,严云生有时也在心里琢磨,不知道蒋小福眼见自己的本事,会不会后悔呢?他暗暗希望蒋小福来挽回自己,可惜等了好些日子,连面也没见着。这日,严鹤到春景堂找蒋小福。来得不是时候,恰逢蒋小福得了闲,正准备品尝一坛陈年的花雕酒,还没开封,就听周麻子说严鹤严六爷来了,在偏厅内等着呢。蒋小福只好万般不舍地过去。因为惦记着屋里的酒,见到严鹤时,就有些冷淡:“严六爷,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他紧接着又问:“既然来了,是喝茶呢,还是用饭呢?”这里的茶是上好的碧螺春,寻常人来喝茶聊天,即是所谓的“打茶围”,并不需要花钱,若是摆酒,那就少则几两,多则十余两,不仅有酒,还有白粥、干果、小菜,统共几碟,不算丰盛,但样样都别致可口,就是京城里有名的饭庄也比不上,价格自然也不是寻常人付得起的。严鹤正待回答,蒋小福又开了口:“时辰不早了,不如就在这里用饭?”这回严鹤不准备开口了,单是含笑点头。蒋小福招手叫来周麻子,低声吩咐了几句。周麻子答应着出去,吩咐小厨房备饭。接着,两人就相对无言起来。蒋小福忍不住撩他一眼:“六爷来了,怎么又不说话?”严鹤一直看着他,这时就很有涵养地一笑:“我怕蒋老板还有吩咐,不敢打断。”蒋小福遭了戏谑,微微有些脸热,嘴上却是不肯承认:“哪有什么吩咐,不过六爷难得来一趟,我得好好招待。”“的确是头一次来。”严鹤没有计较,换了话题:“我那行二的兄弟,大概是常来吧?”“二爷嘛……”蒋小福另有话说:“说到他,我倒有个问题要请教。”“请说。”“那我问了,六爷可别见怪。”蒋小福道:“你们一个在京城,一个在广东,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儿去,怎么还称兄道弟,好像一家子亲戚似的?”严鹤不紧不慢地回答:“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并不是真的亲戚,只是我来京之后,恰巧帮了他一点小忙,后来走动起来,他又帮了我一点小忙。一来二去,彼此熟悉,我们又是同姓的本家,干脆就以兄弟相称。”讲到此,严鹤一笑:“其实,我也有一个疑问想请教蒋老板,但又怕你怪罪。”蒋小福与他谈了这些话,认为这人有问有答,还算诚恳,于是就很大度地说道:“请说吧!”严鹤道:“前些日子我与严二吃酒,他喝了个伶仃大醉,不免说些胡言乱语的酒后闲话,我仿佛听他提及了蒋老板的名字,这就让我有些好奇,蒋老板与我这位兄弟似乎是情谊深厚,很有些牵绊,却不知其中有什么故事?”“这个……”蒋小福一时语塞,因为知道严云生有些酸腐文人的习性,喝醉后更易胡说。他生怕一言不慎,引出什么倒掉牙的话来,只好干巴巴地答道:“二爷嘛,是个戏痴,梨园行的人,他没有不相熟的。”严鹤“哦”了一声:“那么,唐大人也是戏痴吗?”蒋小福见他言语愈发直接,心里就不高兴了:“原来六爷今天来,是为了拿我消遣?”严鹤来春景堂,的确是消遣来了。入都第一日,他就从别人口中听过逛堂子闹小旦的乐趣。别的不提,单说在堂子里打茶围、饮酒、摆饭,与戏子消磨时光,乃是众人口中一件极乐的事情,正是天上人间绝无仅有的温柔乡、销魂处。他与唐衍文已然是谈不拢了,所以今日才没有顾虑,也来感受一番。不过此时此刻,他瞧一眼蒋小福,没觉出温柔,再扪心自问,也没觉出销魂。受了蒋小福的责问,他很谦逊地发问:“请蒋老板体谅我不懂规矩吧,南边儿虽然也听戏,但没有京城里‘打茶围’的风气,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呢?”蒋小福心想,这是到我这儿做学问来了。他拿出待客的耐心:“六爷,人活着,就要找乐子,有人陪着喝茶清谈、饮酒行令、说笑听曲儿,不是件极好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