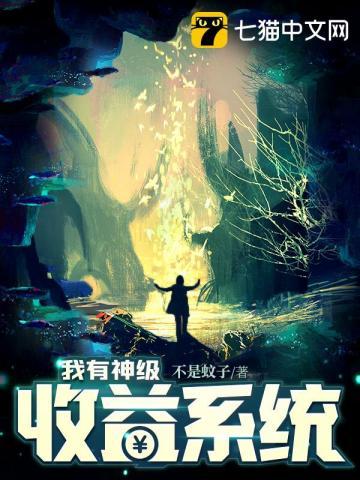秃鹫小说>威臣羽毛球拍 > 第193章(第1页)
第193章(第1页)
恼怒、恐惧、不安、焦虑……无数种情绪在周梧内心翻涌,而许久之后,他终于也渐渐镇定下来。
陈近的无能毁了他原先的计划,周梧觉得自己本该愤恨异常,甚至暴跳如雷,可不知为何,他竟然迅速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在他内心深处,对于接下来将要修改成型的新计划,是隐隐感到期待而兴奋的。
“确实,我们等不到那会儿了。”
周梧沉声说:“皇帝反感立太子,此事若想要办成,需得耗费不少的精力与时间,可并州的叛乱随时都会爆发——我们只能速战速决。”
两人彼此对视,这一瞬间,他们都从对方的瞳孔中看见了熊熊燃烧的野心与欲望。
静默了一会儿,陈近开口缓缓说:“此次在并州参战的将士,我以犒赏为名,已尽数带至京郊,不过统共也只有五千人,而洛京城中却有两万羽林军……”
“已经足够了。”周梧断然道:“皇帝长住北君山,届时以这五千兵马隔绝北君山与洛京的联系,只要确保皇帝的命令出不了北君山,洛京城中就再无能发号施令者,羽林军群龙无首,就只是一群摆设。”
“我们再当面上奏,让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太子一立,则大局定矣。”
太子既立,便是名正言顺,若帝王有恙,太子监国、继位,都是理所应当。出言质疑之人,都可被打为谋逆篡上。
陈近忽而咧嘴一笑,“长公子,从今日后,你我可就成了乱臣贼子了。”
“哪儿有什么乱臣贼子?”周梧也沉沉而笑,“这世间,只有成王败寇。”
庭院深深,酝酿其间的阴谋诡计并不为外人所知,纵使文照得以窥见其中一二,却也万难猜到,陈近与周梧正打算着趁自己带着兵马一离开就发动兵变。
此来洛京行程紧凑,文照拜见过皇帝姜望,再匆匆拜访了老师陆陵及京中的亲近长辈友人,又上朝与陈近同受嘉奖后,便带着已受赏的一千凉州兵离京回返凉州。
待文照离去后,姜望自觉任务完成,他本该再度悠悠乘车回到北君山,不知怎的却突然想到了文照虽率兵离去,可大舅子陈近还带着刚受赏完毕的五千军士驻扎在城外呢。陈近倒也跟他提过一嘴这个事儿,说是将士们在并州连续征战尽两年,想在京郊多休养几日再各自返乡
姜望当时觉得,只是区区五千人而已,算不了什么,随口答应了。
可如今再一想,洛京城中虽有两万羽林军握在自己手中,可北君山却是实打实的守备空虚。疑心病是每个正经皇帝的职业病,姜望也不例外,他虽然不认为自己那个老实巴交的大舅子能生出什么风浪,但时时的谨慎却也是必要的。
于是姜望下令回宫。
帝王车架缓缓停滞、掉头,浩浩荡荡向皇城行驶而去。
漪兰殿中的陈贵人在听闻皇帝回返的消息后骤然失色,“什么?你说陛下回銮?!”
陈贵人的心腹侍女道:“千真万确,陛下的车撵已过朱雀门了。娘娘,是否要通知大将军,行动暂缓?”
“不可!”陈贵人断然摆手,“文照已经离去,陛下只应允兄长的兵马在京郊多休整两日,若再借口拖延,只怕陛下立时就要起疑心!再者,并州传来消息,那头的叛乱越闹越大,今文经学派的人,就要压不住了……”
陈贵人一张俏脸森寒,圆圆的杏眼中寒芒一闪而过,“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城门校尉张廉不是周淮那老匹夫的门生么?这等时刻,也该轮到他出手了。”
……
宣室殿内,虞泽适时奉上一盏汤药,“陛下,该喝药了,自陛下开始服用原平侯进献的药方后,咳疾缓和了不少呢。”
姜望“嗯”了一声,“长明送的东西确实有效,近些时日体内的躁郁之感平息不少。”他刚刚接过药盏,一身轻薄纱衣的陈贵人忽然摇曳而入,虞泽立即深深躬身不敢直视。姜望见状,登时放下药盏,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陈贵人,“最近倒是甚少见你穿得这样艳丽。”
“陛下,”陈贵人腰肢轻摆,缓缓躺入姜望怀中,一双美眸潋滟生光,“陛下只顾宠着新来的妹妹们,哪里还记得上一次见妾是什么时候?”
姜望调笑道:“胡说,分明七日前才见过。”
陈贵人幽幽叹息一声,双臂如灵蛇般缠绕上姜望的脖子,在他耳边娇嗔:“陛下都已七日未给过妾快乐了。”
姜望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自开始服用文照进献的汤药后,对于五石散和男欢女爱的欲望淡褪了不少,如今陈贵人蓄意勾引之下,那股熟悉的邪火再度从下腹窜起,姜望顺势将药盏往虞泽手中的托盘上一放,反手将陈贵人带到了塌上。
女人轻盈婉转的娇笑声中,淡紫金色的帷幔重重落下。虞泽无声地长叹,端着药盏躬身退下。
不多时,帝王塌间便已凌乱狼藉一片,可姜望额前汗水涔涔,眉头紧皱,数日未服五石散,身体虽平和不少,却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在此关键时刻,竟然使不上劲儿。
“陛下,这是怎么了?”陈贵人眨巴着眼睛巴巴地看着他,状似关切地道:“若是陛下体力不支,不如今日就算了——啊!”
姜望在陈贵人颈间不轻不重的咬了一口,“算不算了的,可由不了你!”说罢,姜望强撑着起身,取出暗格中的五石散,熟门熟路地服下,随即再度欺身而上,
陈贵人像风铃一般的笑声在随夜风出很远,直到半夜时分,笑声戛然而止,陈贵人瞪大了一双杏眼,借着室内昏黄的烛光观察姜望青紫一片的脸色,“……陛下?陛下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