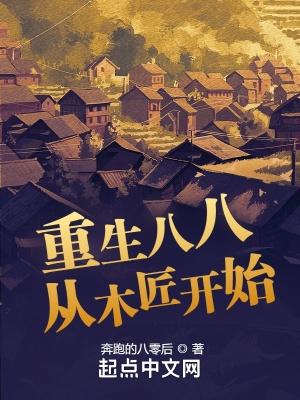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折枝思故人 > 第6章(第1页)
第6章(第1页)
在一个不起眼的茶馆裡,庄伯修自顾自地玩著拨浪鼓,“一月之期已过瞭十天,不知道他此番进展如何呢?”
破局
姒宣彧手下有两员大将,皆是心腹:朱雀和帝江。
帝江武功过人,魁梧粗犷,刻板固执,不解风情,常伴于姒宣彧身旁,负责守卫。
朱雀工于心计,处事谨慎,心细如发,演技超群,相貌柔美,常常和姒宣彧打配合战。
他二人威名,自是衆人皆知。是以杨庆从地牢裡缓缓转醒之时,见到朱雀,顿时吓得哭爹喊娘,抱著地牢的承重柱不肯撒手。
杨庆虽说有左相这个后台,但是谁知道姒宣彧这个疯子想干什麽。进瞭地牢,一时半刻也出不去,这地牢裡七十二道刑罚,可不是说笑的。
真要惹恼瞭他们,便是要蜕一层皮,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自己!杨庆哆嗦著,脸上的横肉都在颤抖,隻盼著朱雀能高抬贵手,先不要动刑。
朱雀虽美,然他笑肉不笑地盯著杨庆,亦是十分可怖,让人生不起半分旖旎心思。
“大大人,草民实在不知那洛小女子竟是姒监大人手下,要不借草民十个胆子,也不敢和姒监抢人啊!”
唉,坏就坏在自己不该色胆包天,竟为瞭一个女人傻傻地找向那座宅子。杨庆恨得咬牙切齿。
朱雀低下头看著他,“你不是知错瞭,你隻是怕瞭。”
朱雀又怀裡摸出连封面都发黄破损的本子,在杨庆面前用力的扬瞭扬,本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你猜这是什麽?账簿!我告诉你,左相已经自身难保瞭,你老老实实交代,把知道的都说瞭,兴许陛下还能饶你一条生路!”
朱雀半张脸在地牢的烛灯下映得惨白,半张脸掩在阴影裡,将那本僞造的账簿甩给杨庆看,看著他脸色青白交错。
“我,我其他的都不知道,舅舅他们有什麽事也不会告诉我这个废物啊!”杨庆用力回忆著,“庸黎,庸黎你晓得不?我偶尔碰到他去舅舅傢做客,舅舅还叮嘱我不许乱说。”
杨庆哭丧著脸,攥著朱雀的衣袍下摆,“你去抓他,我什麽都不知道,你放瞭我吧!”
朱雀厌恶的一脚把他踢开,合拢牢门上瞭锁,转身离去瞭。他的影子被越拉越长,越拉越长,重影交叠,直到消失不见,和阴湿黑暗的地板融为一体。
“依著您的吩咐,竟然诈出瞭,”朱雀皱瞭皱眉,“庸黎。”
姒宣彧翻著兵书的手也停下瞭,过瞭一会儿才开口:“一人之词,不可尽信。庸黎是庸洲的族兄,此事我得向顾大哥细说。”
“本来也没想著靠一本假账让他认罪,左相行事确实也不带著杨庆,就看我赌的对不对瞭。”姒宣彧风轻云淡地说,好像那个为期一月的倒计时不是针对他的一样。
顾慈钧自然是不信庸洲会和庸黎一起叛去左相旗下,更不信姬令会任凭连坐制度残害忠良,还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庸洲也是如此。”
帝江派人敲打敲打瞭庸黎,怎麽看都是指著左相去的。左相是百思不得其解,庸黎是私下投奔他的,又藏的隐秘,到底是如何被姒宣彧察觉的?
有人提醒他,他外甥杨庆前两天因强抢民女被抓瞭。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傢伙,恐怕被吓瞭一下,便什麽都说出来瞭。他们打点瞭狱卒,听说朱雀来过,还有什麽“账本”之类的争执。
左相脸色瞬间凝重瞭,“甚麽账本!他姒宣彧真是急糊涂瞭,以为拿假账就能让我倒台吗?他就是屈打成招按著杨庆摁瞭手印又怎样,老夫不认!”
左相站起来在堂屋裡来回踱步,气急道:“你去告诉杨岳,看他养的好儿子,敢来攀扯我瞭!出瞭什麽事,他自己想办法吧!”
这便是要弃卒保车瞭。虽说杨庆知道的不多,但终归也有洩密的风险,不能让他误瞭大事。
吏部侍郎杨岳一早就备瞭礼候在姒宣彧门外瞭。上午的太阳也确是不留情面的,杨岳已是满头满脸的汗。
姒宣彧略带怜悯地看瞭看他,“今年春闺,杨大人卖官鬻爵的钱,怕是都带过来瞭吧?你也真是舍得,不过为瞭亲儿子,有什麽舍不得的呢?”
杨岳也隐约听过账本的事瞭,被这麽一诈,差点给姒宣彧跪下。
姒宣彧把那本僞造的账本抛给他看瞭。
杨岳胆战心惊,快速翻动著,喃喃道:“卖官鬻爵,两万两白银。郢城重修官道,一万两白银。去年,赈灾粮,三千两白银”
“大人明鉴!微臣实在没有贪下这麽多啊!”
账本是捕风捉影来的,裡面记载的当然不全不准。姒宣彧还特意叮嘱朱雀往多瞭写,千万不能比实际数据少瞭,不能让杨岳发现可疑之处。
姒宣彧似是安慰:“你与颜衡合作,实是与虎谋皮。这本账簿就是他提供给我的,他自己贪的还有他其他党羽贪的,有可能败露的,通通都栽赃给你。”
“但是呢,”姒宣彧话风一转,“本官自然不是徇私枉法之人,倘若你能提供准确的账本数据,可以考虑减刑。”
杨岳本不是个草包,隻是他儿子前脚关进地牢,颜衡右脚就派人来要把他踹掉,又告病闭门不出。当下,他还有极可能被巨额的贪污数字送上断头台。
杨岳嗫嚅瞭许久,终究是认瞭,把他所知道的颜衡的恶行一笔一画写瞭下来。离开姒宣彧府邸时,杨岳迎面遇著太阳刺目的光芒,忍不住淌下泪来。
得瞭姒宣彧此番助力,姬令笑瞭笑,单独留颜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