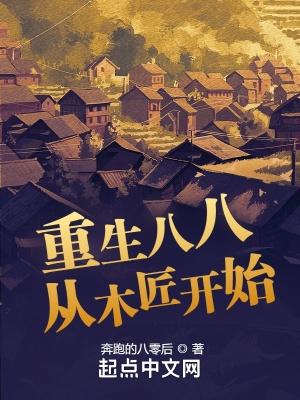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一如既往的沉默什么意思 > 第93章(第1页)
第93章(第1页)
两双不同颜色的眼睛透着淡淡的月光对视。
山姆不耐烦地对着卧室喊:“你他妈的钱到底花在哪里了?”
过了半分钟,保利的声音传来。
“不知道。”他说。
保利不情不愿地让出自己的大床,拉着被子躺到沙发上。山姆自愿睡在大床靠墙的那一边,给汤米留出大片空位。躺在床上,汤米再次进入浅眠,没过过久,他又感觉大腿内侧发痒,仰头一看,山姆·特拉帕尼的手都快伸到他的□□里,而山姆本人还在呼呼大睡,他和保利的呼噜声快将房顶震塌,窗外天色微亮。不可否认,那是段幸福的日子。
站在保利的公寓楼下,他差点认不出来这里,土黄色的天笼罩之下街道的墙壁变得失真,河水泛着油腻的光。门口坐着两个无所事事的人,一男一女,男人戴着眼镜,脸上有雀斑,女人头上包着红底白圆斑的丝布,嘴里念叨着什么,汤米走进时听清楚了,她在抱怨清晨巨大的动静,这个街区已经很久没有新鲜事了,每个人都死气沉沉,这种事情她可吃不消,男人抠弄着自己的指甲说她胆小怕事。
公寓大厅有一股煮白菜的味道。走到一楼的楼梯口时那味道最为浓烈,想必是住在楼梯间的人在做自己未来一天的吃食。顶灯坏了一盏,墙上布满浅黄色的水痕。宽阔的走廊的两侧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杂物——清洁工具,单人床垫和水桶旁边立着已经干了的拖把,下面还压着包装纸片。床垫烂了一个大洞,沾上不知名黑渍的弹簧和黄色棉花迸出,故意为之的破坏让他不再具有修复的价值。汤米往楼上走去,他来过这里许多次了,那些杂物的位置几乎从未变过。保利·隆巴尔多的房间在二楼的最里面。
门留有一条四指宽的缝隙,汤米敲门的手停在半空,离门板就差那么几毫米。他手腕一转,五指碰在门板上,另一只手伸进大衣,从侧腰掏出枪对准屋内。轻推木门,足有枕巾那么大的血泊垫在保利·隆巴尔多的头颅下,血迹顺着木地板的纹路向四周蔓延,末端已经被木地板吸干,保利的太阳穴赫然是一个漆黑的子弹洞,暗红色的血从掀起的皮肉里流出,空洞的眼睛盯着汤米的皮鞋。
保利·隆巴尔多死了有一会儿了,身上还穿着睡袍。汤米枪口对准屋内,试探着蹲下摸了摸朋友的背。保利确确实实是死了。无论他多么想抱着朋友还有些温热的尸体替他落泪,他都不能这样做。
河上的冷风从开了一半百叶帘子的窗户刮进来,摸上汤米的手腕,掉落在地的报纸抖动着滑到汤米的脚边,他踢开报纸,压着脚步,紧紧捏着手里的枪。左脚的脚跟对准右脚的脚背,右脚脚跟抬起,慢慢落在左脚的前面,手枪从左肩滑至另一头,他用眼睛扫视着,始终保持着腰射的准备姿势,如此狭小的空间,只要面向敌人扣下扳机,子弹十有八九都会掉进敌人的身体里,他从门口巡逻到客厅,又漫步进保利的卧室,检查每一个可能藏着凶手的角落,床垫下,衣柜和浴缸帘后也不放过。屋内仍是一片死寂。
他汗水洇出的指印抓满屋子所有能找到的盒子、储藏柜和木箱,保利的生活用品少得可怜,为数不多的东西都被他翻到地上,除了几个人为破坏成缺角的硬币,他就只找见了几个包装纸片的斗笠状碎屑,本该像主教堂外墙上仅作装饰的小型罗马柱一样整齐排列的打捆钞票消失都不知所踪。
钱也不见了。
丁零零——丁零零————
突如其来的铃声让汤米心头一紧,他背靠墙壁,透过百叶窗侧身向外看。
街上空空荡荡,自己的天蓝色v810待在路旁,门廊旁闲聊的一男一女,两个脑袋碰在一起。垃圾桶旁有三四滩已经被风吹干了的呕吐物。驼着背的老妇在河岸边走着,身后跟着她的孩子,船只上的旗帜在飘扬。
丁零零——丁零零————
铃声催促着他快些将电话接起,汤米再次瞟一眼窗外,跨到电话机前,拿起震动着的听筒,抵在自己耳边。
“坏事了,保利!”
这是山姆·特拉帕尼的声音。
“他死了。”汤米说。
电话里传来惊诧的喊叫。
“就在我眼前,他倒在走廊上。操他妈的头上被开了两个洞,尸体还没发硬。”汤米用食指按压自己的眼角,由于干涩,眼角发出挤压海绵时才有的出水声。
“我天,我就知道!但还是晚了一步,本来是想打电话警告他的,我的老天……萨列里!萨列里发现你们抢银行的事情了。”
汤米在见到保利尸体的那一刻就猜出事情的大概,但山姆·特拉帕尼的话还是像连环炸弹和一战巷子里随处可见的绊雷,将他的思考时间炸得四分五裂。
“保利被杀是他的清除异己的第一步计划,你也自身难保。你得趁着别人不知道赶快消失。”
“汤米,你还好吗?”
“保利死了……钱也不见了,全是萨列里搞的鬼。”汤米扶着额头。
“我告诉过你们!不要试图去改变。”
“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山姆。我现在缺点钱离开这里,你能替我解决吗?”
山姆似乎对他的请求早有预料,汤米话音未落,他就赶忙接上:“要什么都行,咱们是兄弟,有需求时在所不辞。要我现在来保利家里吗?”
“不,不。我不能待在这……美术馆,我们在市美术馆见面吧。”
“保持低调,”山姆说,“替我和保利好好道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