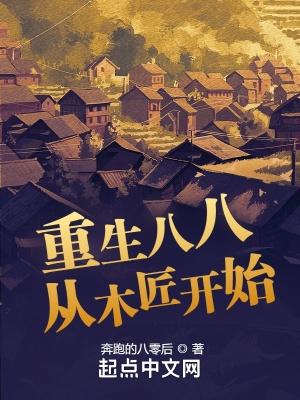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一如既往的沉默什么意思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说来话长,总之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压低声音,凑近她。
“不会有什么事?”她突然提高音量,“你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要把佛洛依接到你身边?”她皱起眉头,直视着汤米,“我就这一个孩子。”
“我没有这层意思,”他握住姐姐的瘦弱但粗糙的手,看着和自己相似的眉眼,温和地说,“这屋子太拥挤。我可以每个月给钱,让你们住在更好的屋子里,在霍尔布鲁克或小意大利。”
“不行,绝对不可以。”她看向紧闭的卧室门,顿一会儿,她说,“托马斯,我们不能总靠你来养活。”
“我们是亲人啊,贝拉,你什么时候变成美国人的性格了?”
“这跟美国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戴维斯?”她睁大那双和她已故父亲一模一样的绿眼睛,“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把当混混作为职业,尽管这能给你带来诸多钱财,母亲知道后,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又不是去圣米耶勒打仗。我的工作没别人讲的那么的……”他顿住了,褐色的眼珠转向光源,蜡烛的火苗爆发惊人的威力,烧着了房顶——滔天的热浪向他的面中袭来——短暂地痉挛。闭上眼,再睁开,火苗恢复了温顺的常态。“……那么危险。”他近乎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你说什么?”她没有听清楚弟弟的话。
他的视线再次回到贝拉身上,“别告诉妈妈,行吗?”
“瞧瞧你穿的——活脱是个混混……”她想要叹气,但只是捂住了半边脸。
“贝拉……”汤米试图解释。
“托马斯,哪怕你是一辈子都是个司机,也比天天去讨债打架更安全,也更受人欢迎。”伊莎贝拉最终还是将心中的憋闷以叹气的方式抒发出来,她看向餐桌上的蜡烛,蜡烛被窗外的风吹的摇曳。她默默地说,“我想和你说别的事。”
听到这里,汤米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叫道:“他又打你了?!”撸起姐姐的毛衣袖子,借着蜡烛光搜查是否有伤痕。只有偏白的皮肤和儿时的旧瘢痕,他手上松了些力道。
“老天呀,别激动!你把我吓得不轻,汤米。自那之后他不再打我,他说要和我好好生活……幸亏有你。”她抽回手,拽下袖子。
汤米抱着伊莎贝拉的头,吻了吻:“如果他以后还打骂你,千万要告诉我。”
“我会的,汤米。他不会当着妈妈的面发脾气的。”她揉捏着汤米的耳朵,安抚他,“今晚留下来吧,我和你可能有别的话要讲。”
“恐怕不行,贝拉,我明天早上得去酒馆。”尽管他想和贝拉说很多。
吱呀一声,卧室门开了一个缝,佛罗伦丝探出脑袋。还没等她的外婆开口将她哄回去,她以委屈又微弱的声音说,“我们不能去马戏团了,对吗?”
“听话,佛洛依。”她的外婆在哄她回去。
“很抱歉,孩子,”汤米说,“舅舅明天要去上班,这是舅舅的工作,我们下周五去马戏团好吗?”
“真的吗?”
“我保证。”他走过去,蹲下揉揉佛罗伦丝的脑袋,又起身亲吻母亲的嘴角。
“别和伊莎贝拉聊太晚。”母亲笑着说,抱起佛罗伦丝回到屋里,关上门,留两个子女在客厅。
他们又聊了十几分钟,伊莎贝拉把汤米送到门口。
“无论怎样,你都要过的安定,这是我们的愿望。”在汤米临走前,她的右手摩挲着他的脸,“你总会明白的,汤米,你总会明白的……你是儿子的儿子,将来也会是父亲的父亲。”
“我明白……贝拉,我明白。”他俯身轻贴上姐姐的脸颊,“再见。”
“愿上帝与你同在。”
他在走到拐弯处时转身,街道尽头是伊莎贝拉在门口的暖光映衬出的黑色剪影。
回到家,汤米脱掉皮夹克,扯开领带,把它们扔在藤筐里,连衣服带筐都踢到角落,接着他解开衬衫,退下裤子和袜扣。躺在床上时他身上仅剩条纹短裤和一件洗的边缘脱线的背心。他辗转难眠,只好起身点了根蜡烛,拉出餐椅坐上去。乳白的蜡烛泪一滴滴流到铜台中。汤米从食品柜里拿出一本旧书。屋子的前任房客留下的东西被装在一个麻袋中,而一本由俄罗斯语翻译过来的旧书就静静地躺在几件烂布中,他把它拿了回来。他越看越精神抖擞,意识到行为的反常后他把书扔到椅子上,楼上的脚步声凌乱,还有孩童的大笑,接着是女人的大吼,没过多久所有杂音都停了下来,他的呼吸也慢慢平静,眼睛因为蜡烛的光照而酸涩。他吹灭蜡烛,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盖住下半身,不一会又觉得燥热,扯起被子塞在身体与墙壁之间。初秋的冷风吹进来,他再次起身关上半个窗户,留下离他远的那扇。泛起的困意现在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站在半个窗前看深蓝的夜空——房子的朝向在这时候看不见月亮,她在这栋楼的后面,银粉洒在高低起伏的屋顶,悬挂在对面楼窗户的镂空置物台和上面的花盆阴影落在亮晶晶冰块般的石子路面上。低矮的楼宇簇拥着教堂,尖顶下方的玻璃窗散射着钻石般的光,道路的尽头传来狗吠。后半夜空气有些冷了,他揪起椅子上的衬衫披在肩上,心神不宁的汤米任凭各种平时并不在意的琐事将自己折磨到太阳破晓时才倒在床褥,安心地闭上眼,伴着熹微的晨光浅眠。
水面赠予的薄雾飘浮在城里久久不散,鹅黄的第一束弱光涨满大街小巷,不出半个钟头这座城将完全苏醒。微冷的风流过快步疾行的哈蒙·辛奎马尼的脸和耳朵,鼻子凉凉的。小意大利与工区的交界处比北方公园要好太多,他居然开始认为这是个好差事了。走北方公园附近的第四大道时,他都要安慰自己:所要经过的腐烂瓜果堆成的垃圾山以及残破不堪的铁皮瓦房只不过是在视线中出现一秒。今年夏天的时候那里臭气熏天,因为有些人直接把粪水泼在路上。每次他从奥克伍德开车到那里,他巴不得用浆糊涂满所有车子的缝隙,可真正的硬汉不会因为路途的‘坎坷’而放弃今天萨列里先生下达的任务。是的,他会绕远路——走中城区和中心岛的链接桥,绕过帝国银行后再次经过一座大桥就到小意大利。平日里他绝不会直行走第四大道至朱利亚尼大桥,尽管这会缩短近十五分钟的车程。刚刚哈蒙将车子停在路边,距离圣丹尼斯教堂还有一个街区,他的任务就是找到住在这个街区的托马斯·安吉洛,将大先生的指令送达,门牌号也许是0122,可他已经在这里走了十几分钟,一直在转圈——他已经连续见到两次靠在报刊亭旁边的电线杆的一个红发青年,前两次他在抽烟。第三次,青年按耐不住心中的瘙痒,跑到哈蒙面前拦住这位不属于街区的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