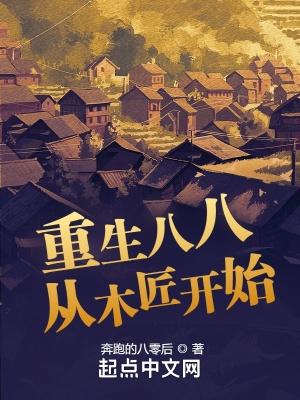秃鹫小说>抛弃作精小祖宗后笔趣阁最新章节内容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余娇娇瞥了她一眼,银台顿时不说话了,反倒是余娇娇又叹了口气。
“你平日不是最不喜他的吗,怎么今日反而帮他说话了?”
“奴婢的确不喜欢他,也不是帮他说话。只是看主子连日睡不好,担心得慌。”
银台道,“主子明明很喜欢沈神医,为何非要送他走呢?”
余娇娇捶胸顿足:“他在我们余家花了那么多钱,这么个祖宗留下来做什么?”
银台听她嘴硬,也忍不住嘴角抽搐:“咱们余家又不是养不起他,沈神医每周也在医馆治病救人,也算是抵钱了。再说,人家沈神医好歹救过您一命,您又如何是视财如命的人,何必用这些违心的话当借口呢?”
余娇娇放下茶杯垂眸:“你这是什么话?”
“奴婢只是觉得主子在生意场上向来雷厉风行,运筹帷幄,甚少有如今这般踌躇境地。您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为什么不承认呢。往日您总想着找个皮相好瞧着满意的,如今好不容易来了个合您心意的,您却又非要撵人家走。”
“谁说他合我心意了。”
“您瞧沈神医时,眼里都是笑意,对着其他人可没见如此。”
银台叹了口气,“主子,您可真够拧巴。”
说罢,她也不再劝诫,收拾了茶具便要退下,却见门外急匆匆撞入一个人影。
“银纹?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银台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身影惊讶道。
银纹却没空理会她,越过房门朝余娇娇单膝跪下复命,眼中满是愧疚:“主子,属下办事不利,未能将沈神医平安送到百草谷。”
余娇娇手一顿:“如实说来。”
“是。属下原本按照您的指示绑着沈神医一路到了禹门,可是在驿站时,沈神医说他身体不适,属下就将他的绳子解了。结果晚上用膳后,属下觉得昏昏沉沉,再醒来时,沈神医和马车就,就都不在了。”
他说完也羞愧得很。
主子让她看好人,一定要将人平安送回百草谷,结果他却一时大意被下了药,还让人跑了。
余娇娇这几日本就没睡好,此时头疼愈加,伸手抵着太阳穴蹙眉安慰。
“这不怪你,起来吧。”
她又长叹一口气,“沈献既然要离开,应该也有他的谋算,他为人聪慧机警,应当应当没什么事。”
银纹:“可”
可当初沈献就是被人卖到青楼,才和他们遇见的啊。
真的没事吗?
余娇娇自然也想到了这儿,头更痛了
平日里沈献自然天不怕地不怕,可他每月毒发之时便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再加上他那淬了毒的舌头,天生得罪人的好把式,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就被人给记恨上了。
余娇娇让自己不要再去多想,人生在世,多的是来路过客萍水之交,沈献既然要自己离开,那她也无法阻止他。
马车上银钱被褥皆有,就当是春风一度的报酬,她也不算亏欠了沈献。
自此之后,桥归桥路归路,万事与她无关。
这样想着,余娇娇也说服了自己,打算一切皆是浮云去,回屋补觉最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