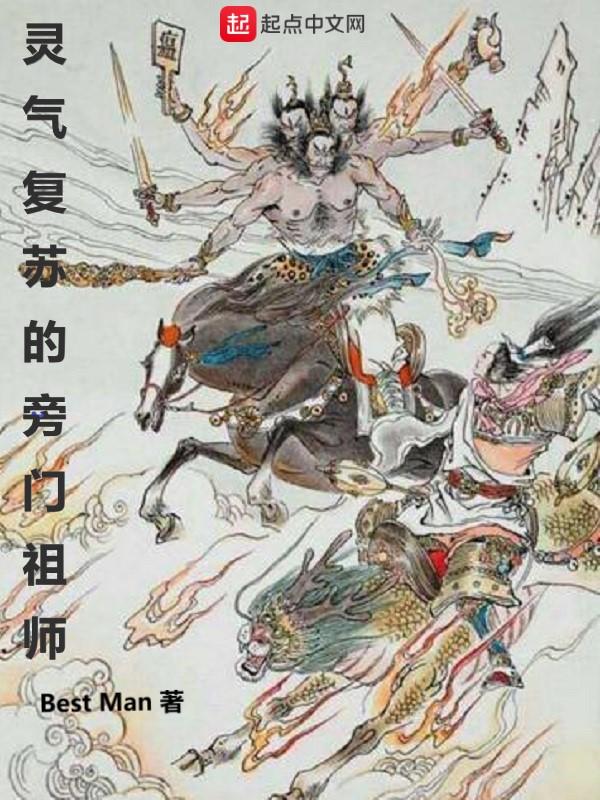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春光袅袅 > 第30章(第2页)
第30章(第2页)
这些日子以来,他屡屡纠缠,日渐放肆。
如今更是堂而皇之,如入无人之境地,睡在她的卧榻之侧,然而这个男人,就连身份都是虚构的。
宁烟屿心下几分无奈:“师般般,我从未说过,我是封墨。是你以为我是。我不过是并不曾否认。”
离宫相会的夜晚,她唤他“封墨”,他不过是没有否认。
他说:“你真是聪明。”
用那种看聪明人的目光,微微含着笑意,夸赞她。
他还敢说,这不是一种变相的承认?他分明就是包藏祸心!
师暄妍勃然大怒:“你还敢狡辩!”
她将乌木簪刺出,直抵他胸前。
“你若再不说,我就唤人,把你这个逆贼拿下。我想开国侯府,大抵不会放过你这么个勾引娘子的淫贼。往昔我是为了护你,但现在可不会了,你还不老实承认!”
敢明目张胆得罪开国侯的,在长安虽然不少,但也绝对算不上多。
即便是门第旗鼓相当,也要三分考量。
谁知,这男人听了她的话,不但没有半分畏惧,反而淡淡一哂。
他竟然在嘲笑她!
师暄妍气急败坏,乌木簪又抵进了几分。
几乎便要触到他的前襟,目下,已与他胸口的墨线夔纹相距不过半寸的距离。
小娘子就是发了狠,也是心善不敢下黑手的。
宁烟屿坐在她香闺的拔步床上,姿态闲闲,淡淡道:“师般般,你阿耶动不了我一根手指。我早说过,你可以尽情信任我,投靠我,我会帮你。你做不到的事,我能做到,你要不要考虑?”
是何人,敢如此大言不惭?
师暄妍咬着发颤的樱唇,脑中回想起蝉鬓说的那一席话。
太子之命……
巡视河道……
一切巧合,突然应在此处,化作一个清晰无疑的答案。
“你是宁恪。”
少女朱唇觳觫,如墨玉般的美目含了震惊之色,一瞬不瞬地望着纱帘之后的男人。
乌木簪自她的骤松的玉指间一抖,晃荡了一下,坠落在地。
洛阳折葵别院的相逢,原来由始至终是场孽缘,他竟然是宁恪。
少女的眼瞳写满了荒诞和震惊,压抑的情绪,犹如拉满的弓弦蓄势爆发。
乌木簪掉落在两人脚边,沿着纱帘帷幔骨碌碌地滑落,被卷至阶下。
她的身子在发颤,似是冷得厉害,齿关不停地磕碰。
宁烟屿起身拨开帘拢,跨上半步,来到师暄妍的面前。
他的个头,比她差不离要高出一个头,宽肩腿长,整个人似一堵墙面,附着阴影压下,几乎将师暄妍整个笼罩在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