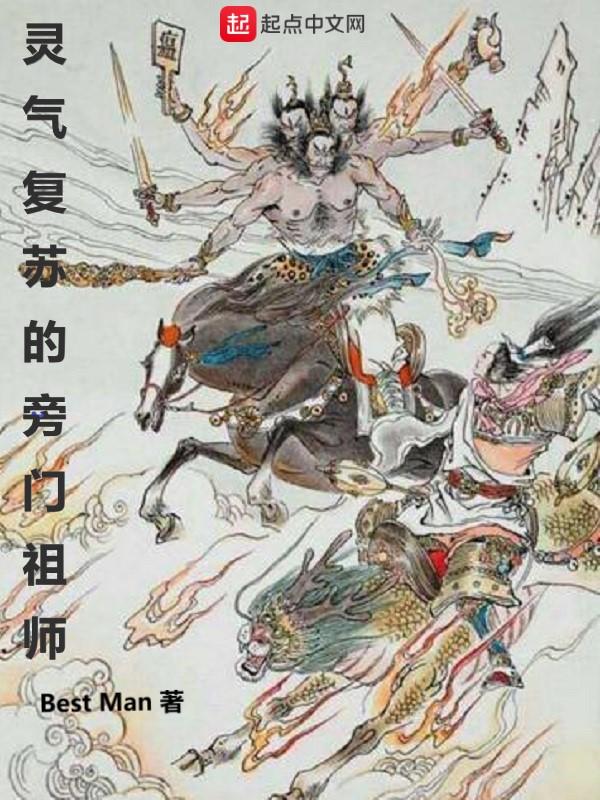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收藏魔王的图片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卫初宴虽然经历过一日一夜的论战已然很是疲惫了,然而一到家中,她便又有了精神,一路寻着赵寂去了,从被窝里捞出自己的娘子,满心欢喜地给她看身上的官袍,并非得意洋洋,只是想与赵寂分享自己的喜悦。
她追求了许久的事情,如今,终于是看到了希望。
赵寂被卫初宴的喜悦感染,这两日一直萦绕在赵寂心中的冷雾消散了些许,她笑吟吟地打量了卫初宴几眼,煞有介事地点头:“嗯,我家娘子穿了官袍,可真是清俊无双。”
卫初宴便又不好意思起来,赵寂一看就愉悦,将她抱住:“给我摸摸,官袍的滋味如何。”
官袍是什么模样,赵寂能不知道吗?然而即便是她做储君做帝王的那些年,也未曾见过有哪个臣子,将官袍穿的如卫初宴这般不落凡俗、风度翩翩的。
醋缸
赵寂倚在床头笑,她招招手,将卫初宴拉到身边,用自己的唇去寻卫初宴的唇,卫初宴的反应十分可爱,赵寂兴起,想拉她上去:“你穿上这墨色官袍,倒别有一番韵味。”
卫初宴却恢复了清明,微微退开了:“不好不敬。”
赵寂挑眉,随即,却是笑了,是了,卫初宴自然不会着官袍做那轻浮之事,她早知卫初宴这人骨子里很有些文人气,对身上这身官袍,是肃穆且虔诚的,与她相比,赵寂眼中的官袍,只是权力的一种工具罢了,是她摆弄棋子的一种手段。
赵寂便又想到,此时的卫初宴,也已成了新帝手中的一枚棋子,她收起笑意,眼中墨色渐深,不知在想些什么。
卫初宴以为她不开心了,过来亲亲她,被赵寂揪住耳朵,又反亲了好几口,直亲得她眼泛春水,含情脉脉。
“做了官,我知你总是想要做到尽善尽美的,便是我劝你手段轻些,你怕是也不会听。且你初入ahref="https:tags_nanguanchang。html"target="_blank">官场,手段凌厉些反而利于立威,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至于你想说的,你这一天一夜在宫中,大约也已掷地有声地说了。”
赵寂认真说了几句,卫初宴初入官场,还懵懂着,凭一腔志气行策,对赵寂的话,一知半解,但也慎重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赵寂观她神色,见她人逢喜事而神采奕奕,就连眼底眉梢都满是喜色,仿佛对入仕之后的事情充满憧憬,赵寂不由在心中一叹。
她想起当初那乞丐的事情,大概也能猜出,卫初宴入仕是想做什么。这是卫初宴自己选择的路,她已在这条路上走了许多年,如今终于走到了峰回路转处,哪怕路上满是荆棘,而尽头布满利刃,她也会一直往前走的。
永熙6月初,卫初宴携她的文章与口舌,像一颗流星一般飞入沉疴已久的朝堂,从此,天要变了。
她蒙召入朝那一日,朝堂众臣先是为她的隽秀清雅而眼前一亮,却在传阅她的文章《人头税十弊十对》《察举制吞人才论》之后,个个面色阴沉,言官李游首先发难,言道“你敢妄论国之税法之不是”,紧接着众臣也争相开口批判着卫初宴的文章,一时间群情激奋,仿佛卫初宴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新帝赵璨对此早有预料,一直蹲坐上首,只拿鼓励的目光望着卫初宴,而卫初宴也并未叫她失望,以“今有人头税,每每征收,既剥小民皮,只去豪强衣;小民困于税,多不养子、无力守地,豪强悠于税,兼并沃土、仓廪渐深。循环往复,地无民耕,物无民买,入口消减,国库渐空,此税之过也”起头,从李游辩起,不卑不亢将众人所持观点一个个驳了个遍,须知众口则杂,然而卫初宴竟能将他们的言辞从头记到尾,且一一辩论回去。
这令众臣惊惧之余,气愤不已,然而又不免为卫初宴感到可惜。
这样的大才,怎就生于微末,不能为士族所用?瞧瞧她要杀的制度,一个人头税,一个察举制,前者是贵族豪强广积土地之依仗,后者是士族长盛不衰之根本,卫初宴一开口便要变人头税为土地税,又要革察举制广开官源,她触犯的不是一家一族的利益,而是整个名门望族的利益。
众臣不由去揣测新帝之意,却难掩惊怒地发现,新帝同样锐意进取,否则,也不会有卫初宴入朝一事发生。
辨,辨不赢,因卫初宴虽抨击现有税制与选官制度,然而她却很聪明,将基点牢牢立于国本,且将人头税中民与国的矛盾转化为日渐富有的地方豪强与日渐空虚的国之间的矛盾,令皇帝去猜忌坐拥大片田地的豪强——且这些豪强多为贵族附庸——由此引出土地税。
赵璨是精明强干的帝王,人头税已将百姓盘剥到无油水,然而土地税却象征着瘪豪强而丰国力,赵璨自然会顺势推动此次变革,至于察举制,也是同样的道理。
卫初宴有关察举制的一个重要论述是:若是士族长久为官,便抱成团,沉淀几朝之后,帝王之言,还有谁会听?
正是这两点论述,令满朝官员不敢过分辩驳,否则,便是彻底将自己抛去帝王的对立面,便要成那“杀鸡儆猴”的鸡。
卫初宴赢了,赵璨当即下令,封她为自己的侍从郎官,却不用随侍左右,而是给她点了官署,又为她调派了许多属官,命她一月内拿出完整的土地税征收制度,先革新税法,若是成果喜人,再进一步改良察举制。
赵璨说的是“改良”,只是安抚士族的一句虚言。卫初宴心中清楚,那位敢于用她的新帝,心中所要的,可不是一个“改良”,她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王权,要一个开辟新制度的贤明帝王身后名,而卫初宴,要的是寒门学子人人都能凭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