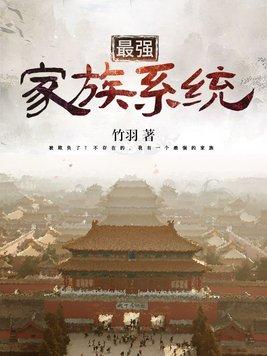秃鹫小说>山中何事? > 第72章(第1页)
第72章(第1页)
汪霁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行吧,也没好到哪里去。
吃过早饭他要去菜地,临出门前符苏从二楼露台上探出头喊他:“你屋里的床单被套我一块儿洗了烘干了啊。”
汪霁戴着草帽仰起头:“行。”
屋后有一颗乌桕树,老树了,这栋屋子从最初的砖墙灰瓦到现在,里里外外什么都变了,只有它没变。
满树的乌桕叶泛黄,在符苏身后摇摇探出枝头。
汪霁转身往院外走。
从杭州回来那天他就想搬回家去住,说出来的时候符苏也没拦他。
等到他进屋开始收拾东西,符苏抱臂倚在门框上,突然吐了口气,听着跟叹气似的。
汪霁叠衣服呢,听见声音愣一下:“…干嘛呢。”
“叹气呢。”符苏说。
衣袖叠出条褶,汪霁道:“我是听不出来你叹气吗?我是问你叹气干嘛呢。”
“不知道,”符苏语气轻飘飘的,“可能两个人习惯了?”又加一句,“我反正习惯了。”
他说完这话转身往客厅去了,剩汪霁在床边愣着。
什么意思啊这是。
“不是,”他抬腿跟上去,“您这话几个意思啊大爷,说清楚。”
“能什么意思,”符苏背对着他往露台走,“你想回去我也不能不点头。”
什么点头不点头?汪霁有点无奈:“有你这么留人的吗?”
符苏转过身:“听出来了啊。”
“听出来什么啊?”
“挽留啊。”
“就这啊?”汪霁简直哭笑不得。
“太含蓄了吗?”符苏轻轻笑了。
“你说呢。”汪霁看着他。
“那我换一种?”符苏说着走到汪霁面前,有几分迟疑,但几秒后,他伸出胳膊松松揽住了汪霁肩头。
声音很低很轻,像有风从汪霁耳边掠过:“有点舍不得,别走吧。”
回想到这儿汪霁抬手摸了摸耳朵,还好,这会儿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