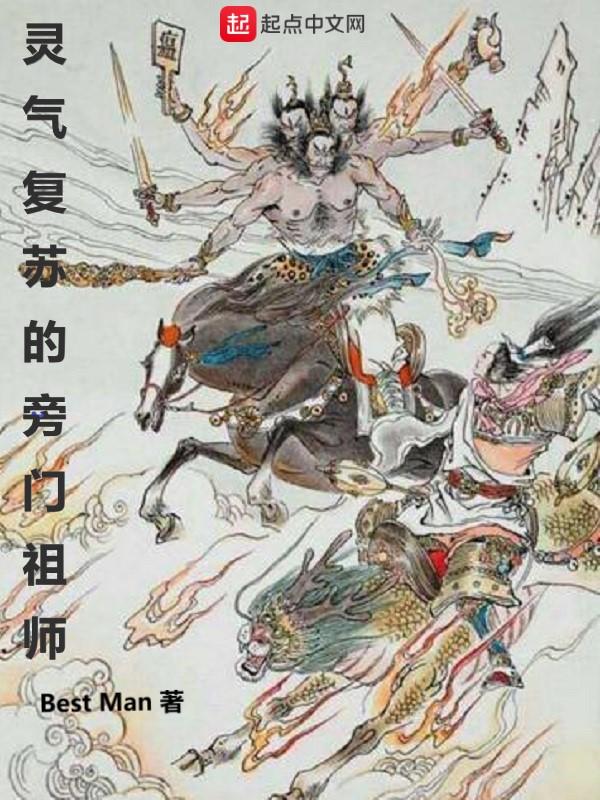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可怜薄命做君王 > 雪护离人行1(第3页)
雪护离人行1(第3页)
想起前夜的事,傅徽之觉得此人大概是南宫雪,虽然此次她不用黑巾而是以帷帽遮面。又瞥见地上的剑鞘,便明白方才紫衣人大概是被黑衣女子的剑鞘击中背脊,才松了一瞬的劲。
他迅速上前助战。没过几招,紫衣人便落了下风。
前夜傅徽之便知南宫雪武艺出众,观此人剑法,若她不是南宫雪,也十有八九与南宫雪同出一门。但若她就是南宫雪,他能感觉出她今日的状态似乎也不是特别好,否则恐怕不须他出手,五招内她便能拿下这紫衣人。
最后黑衣女子逼得紫衣人弃剑的瞬间,傅徽之也已将剑横他颈上。
紫衣人不服道:“两个打一个,算什么?”
黑衣女子道:“我没来之前,你看不到他病着么?你又算什么?”
傅徽之不在意,只问:“谁雇你来的?”
紫衣人道:“我不知。”
黑衣女子抬剑拍了拍紫衣人的手腕,道:“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先废你一只手再说。”
紫衣人急道:“我当真不知!来寻我的人也如他们一般。”他微微偏头看了眼地上那些白衣人,意有所指,“只不过当时是黑夜,那人以黑巾蒙面,不说是谁要雇人,只带了黄金来。我与这些人也是在城外会合的。”
傅徽之对那些白衣人没有下重手,在他们与紫衣人交手时,已逃了大半,眼下只余四五人。
黑衣女子立刻剑指一正在爬起的白衣人,喝道:“那你说!”
不防听见身后傅徽之的声音砸来:“别逼他——”
黑衣女子下意识回头去看傅徽之,只见他收剑过来,她便默契地转将剑对着紫衣人。
方才被逼问的白衣人身子已经开始蜷缩,喉间溢出痛苦的嘶叫,不出片刻,便不动了。
见傅徽之伸手探他鼻息,黑衣女子怪问:“他怎么了?”
“死了。我与他们交过手,只要逼问背后之人,他们登时服毒自尽。”
“对不住,我不知。”
“怨不得你。”傅徽之这才留意到他们身上带的不是弓,而是弩。
他起身,看向紫衣人:“本朝律,弩为禁兵器,私家不合有,满五张便是死罪。”
紫衣人忙道:“我可没用弩啊。”
傅徽之问:“你可有看见他们从何处取的弩?”
“没有。我见到他们时,已弩箭在手。”
傅徽之看向自己的剑,问:“你杀过多少人?”
紫衣人似乎感受到他的杀意,急忙解释:“没杀过无辜啊。”他又看了黑衣女子一眼,道,“这位娘子看起来是游侠,我之前也是啊。遇到不平事,就算没有赏金,也是要杀人的。所杀皆是该死之人。足下也是官府追捕之人,不至于反将我送至官府罢?”
黑衣女子忍不住插话:“何须如此麻烦?直接杀了你,为民除害。似你这种拿钱办事的人,会没杀过无辜?我看你方才那架势,是要置他于死地!”
“我说的句句属实,你们相信我。”紫衣人忽然低声,“何况他也算不得无辜,他是……”他忽地惊叫出声。
黑衣女子猛地偏了下剑,几乎要划破紫衣人脖颈的肌肤。她道:“你身着紫衣,紫衣价高,本朝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你倒是比高官更显贵。”
“你们也看见了,我武艺不差。平日接官府悬赏或私家雇佣,区区紫衣,怎会无钱买?我也只是近日沉溺博戏,失了不少钱,正愁时,遇上他们。他们出手大方,我一念之差,便应下了。绝不会有下回了。”
傅徽之又问:“若我死,你如何向他们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