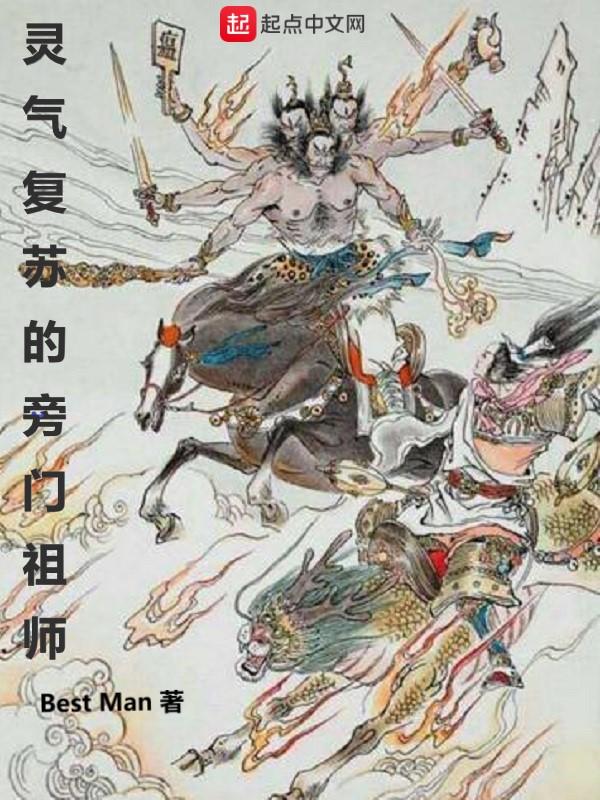秃鹫小说>叹今朝辉煌不在什么意思 > 18画符者(第2页)
18画符者(第2页)
“他给老朽看了易逢机的符谱。”卞中流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带着惊叹的口吻轻轻道,“全本的,符谱。”
卞高震惊道:“易逢机的符谱不是已经散轶了吗?”
“老朽也不知他是从哪得到那本符谱的。”
卞中流转身走进屋内,打开一个柜子,示意卞高把里面的木盒拿出来。卞高擦擦手,无比郑重地打开木盒,只见里面躺着一本黄褐色的古书,封面上写着张狂的五个大字——“天下第一符”。众人目瞪口呆,卞中流抚须微笑道:“老朽当年看到时也很吃惊。也只有符鬼易逢机,才敢如此狂傲啊。”
卞高将符谱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翻开,只消一眼,他便看出这符谱的高深幽妙。他激动道:“这,这真的是。。。。。。”
卞中流点了下头,道:“这就是符鬼易逢机的符谱。当老朽看到这本符谱的瞬间,我就知道自己必然会答应那位贵客的要求。但老朽没想到,他要我画的是九天阙符。”
继符鬼易逢机之后,九天阙符已一千年不现于世。卞中流听到这个请求时,不禁心潮澎湃,心神激荡。他意识到自己久久期盼的机会已经到来,这张符必会成为他今生最满意的作品,不仅他此生无法再超越,往后一千年,也绝不会有任何人能再超越。
他接过了这本符谱,日夜钻研,废寝忘食,画废的符纸几乎装满了一间屋子。整整九年,他全副心神都扑在这张符上。符成之日,他已形如销骨,仿佛将死之人,可他内心的狂喜无以言喻,即使他因这张符衰老了数十岁,满头青丝尽成白发。
他用九年完成了这次朝觐,而后从天才的神坛跌落,认清了自己凡人的本质。卞中流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绝望,他虽穷极一生也无法比拟前人的成就,可他已经竭尽全力去追摹至道,那张九天阙符是他的荣耀,他的证明,他在此刻获得了圆满,虽死,可也。
那位贵客拿走了那张符,留下了这本符谱。卞中流曾试图再画一张九天阙符,但那一张符耗尽了他的全部心神。
从那之后,他再无法握笔了。
“那时我就知道,虽然我画出了九天阙符,但作为一个庸人,这便是我穷毕一生可追摹的极限了。”卞中流叹道,“天才永远是天才,后之来者,再无人能如易逢机。老朽不想你们跟我一样早早地葬送符修生涯,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故老朽原打算等到临终之际,再将这符谱给你们。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见到那张符。不仅如此,它竟被炼进了这枚坠子里,要是老夫猜的不错,这坠子是贮灵珠。除非它里面的灵气枯竭,这张符都会一直有效。”
“贮灵珠?”卞高震惊道,“现在竟还有人炼贮灵珠?”
“是啊。如今世间灵气几近枯竭,那人究竟是从哪找来如此丰沛的灵气的呢?”卞中流感慨不已,“那人真是神通广大啊。”
秦镇邪握紧了拳头,问:“大人可知那道人姓名?”
卞中流摇头道:“不知。”
“那大人可知那道人从何处来?”
“也不知。”
秦镇邪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咬着嘴唇,心中翻涌着不甘。这时,卞高问:“父亲,那这张九天阙符里究竟有什么?”
“安魂,固魂,镇魂,辟邪,除恶,驱鬼,通明,清心,平安,皆安魂定魄,驱邪护体,清明本心之符也。然而唯魂魄有隙,方易招邪祟,唯易招邪祟,方需明本心,要之仍在魂魄二字上。”卞中流望着秦镇邪,严肃地问,“你的魂魄出了什么问题?”
秦镇邪摘下坠子,坦然道:“您请看。”
一瞬间,卞中流就看清了他身上的阴气。他微微瞪大了眼,不敢置信地问:“这怎么可能?”他沉默半晌,微微摇头,长叹道:“难怪,难怪啊。若非这张九天阙符,如何能改天换命,让本应死去之人强留在这世上?然而观汝年岁,至多不过二十,如何能提前三十载为汝谋划?如此手段,非鬼神不能为之。少年郎,你和那道士是什么关系?”
秦镇邪望着卞中流,久久才道:“我跟那位道士,没有一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