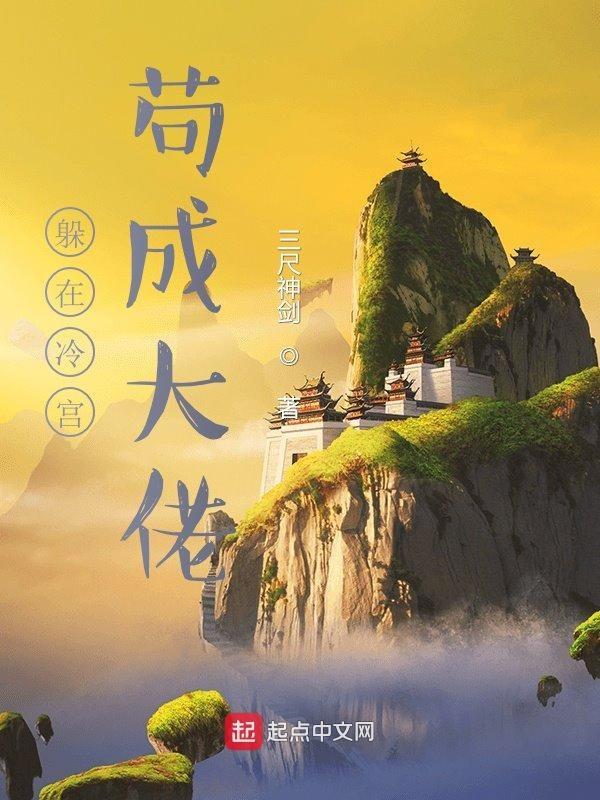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落日陷阱砂梨全文免费阅读 > 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1页)
常年拥有一支完善的医疗团队并非普通有钱人可以承担的。料想这位孟先生家底应该万分殷实。
不过他长年独居于此,几乎无人探望。
护工算了算日子,他在这工作两年多,不长不短,这是第一次见着访客。
访客来头很大,从两排肃立在侧的保镖就能看出端倪。
他跟威廉先生说了。
威廉先生同前一刻听新闻一样,没什么反应。
护工只好退出,告诉门口尊贵的访客,里面的先生已经同意他们拜访。
终于和医生聊完,孟鹤鸣谢绝了陪同。
转头同他那位弟弟,说了这趟长途飞行以来的第一句话:“走吧。”
路周抿唇,跟随在后。
自从抵达大洋彼岸,他就陷入一种奇异的自卑感里。成长到这个岁数,这是他头次走出国门。
以往出现在课本上的单词变成生动的字符一个个跳进耳朵,变得格外陌生。尤其是在见识到他哥的游刃有余之后,他的尴尬和局促愈发增长。
有些生长过程中与之俱来的见识不是通过短暂的金钱堆积便能得到的。更枉论他和他哥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夜暴富和上流老钱之间的差距。
他的财富,本身就是孟鹤鸣带来的。是他作为孟鹤鸣幼弟的附加价值。
沮丧让人心生嫉妒。
他一言不发地跟着走进房间。
这间房正对花园泳池,碧蓝色的水面被夕阳普照,橡树投下一片阴影。盎然的景色与房间里的暮气宛如两个世界。他停在几步之外,看到坐在雪茄椅里的男人——六十多岁的模样,面目自带威严。
他的视线缓缓移过来,先落在他身上,混浊的水色荡开些许清明,而后往前。
“出去。”
在触及到他哥的身影时,沉厚的嗓音只余这两个字。
他哥似乎习惯了,沉缓地笑:“看来过得不错,中气十足。”
男人不理他,视线再度越过他的肩,落向后面。
“你,过来。”
路周知道他在指自己,迈腿往前走了几步。
那些护工大约是听不懂中文,被毫无顾忌地留在了原地。他们低头干着自己的事,对眼前场景兴趣缺失。
最终,他停在数米开外。
他对这位名义上的父亲没有感情,更不了解。
以初见面的印象来看,路周并不觉得黎敏文说得会有用——嘴巴要甜,多叫几声爸,他会记得你的。
他问记得有什么用?
黎敏文说,他不那么喜欢孟鹤鸣,说不定会修改遗嘱。
如今看来,只有不那么喜欢他哥那句话有可信度。
“爸。”路周低垂眼眸,还是这么叫道。
“再近点。”男人混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而后朝另一侧挥手,“你们都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