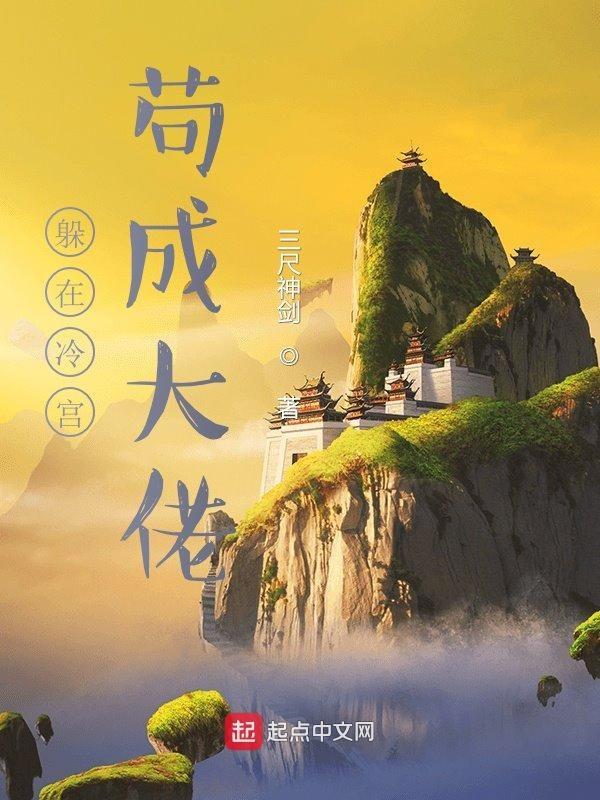秃鹫小说>局部降雨形成的原因 > 第5章(第1页)
第5章(第1页)
窦利钧车里很干净,保养得当,甚至有股似有若无的香味。林平很感谢他出手相助,猛然间意识到自己还没跟他说谢谢,就磕巴着说了句:“谢谢。”
窦利钧瞥他一眼,回道:“不谢。”
至此林平同他再无话可说。窦利钧把他带回了自己家,是个两室一厅独卫大厨房的屋子,比韩元就那间要大上一些。林平初来乍到,不好意思四处打量,窦利钧说什麽他就听什麽。
“热水往左,放一会儿水才会热,小心不要烫到。”窦利钧将柜子里的洗漱用品拿给他,都是全新未拆的,林平又开始说谢谢。
窦利钧在出去之前,歪头看到他耳垂下一点黑,径自伸手上去,抹了又抹,直搓到林平耳垂泛红,烧得厉害。林平缩了下肩膀躲他。他抱歉道:“那是你的痣吗?我以为是沾上的泥,不好意思。”
林平被他摸过的耳朵红到几欲垂血,轻声说:“是痣。”
窦利钧带上门出去,厨房热水壶响起嘶鸣声,他轻快的站在水壶前,撕开感冒灵沖剂,锅上还煮着热牛奶。
林平洗去一身疲乏,脸颊透出自然好气色,站在窦利钧跟前,惹得窦利钧目光深深。“怎麽,怎麽了?”他问。
“你眼睛好红。”窦利钧开口。
林平眨动着双眼辩解说:“是水蒸气。”
窦利钧叫他来喝药,还要喝热牛奶。这会儿窦利钧已经换上居家服,绵软的面料又将他衬得柔和,林平突然很想问问他的年龄,二十六?二十五?那太冒昧了,林平喝光感冒药,觉得浑身上下暖洋洋。
情绪尚未涌上来,林平同窦利钧聊了几句,夜深了便回了屋。林平拉窗帘的时候发现窗外的地面是干的,他又朝树上看,树叶正处于青黄交接,蔫了吧唧,一点没有雨水泡过后的舒展。明明没有很远的距离,连城区都没跨,这边居然一滴雨都没下。林平感到不可思议。
林平只在窦利钧家里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想着带行李走,他想的是先去住宾馆,找到工作以后再去租房子。他把行李箱提起来,这样轮子就不会摩擦地面发出哗哗的巨响。
窦利钧在客厅看到的就是林平那副小心翼翼提着行李的模样。林平也不知道他醒的这麽早,跟他对上眼的时候,似乎感觉到了他的不高兴。
“昨晚上麻烦你了。”林平眼皮有些肿,说话声音哑哑的,窦利钧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偷偷哭过了。
“不麻烦。”窦利钧把手上的书合起来,眼神示意他来吃早餐。
林平坐到桌前,他买的油条还热着,脆脆的。窦利钧吃过了,林平吃饭他也没离席,而是一声不吭的坐着,像是作陪。林平瞥到他手上的宣传册,讲装修的。窦利钧这套房实在光洁,林平昨晚住进来的时候就在想他这个人是不是走极简风,屋子里的装饰寥寥无几,连物件都少得可怜。
窦利钧察觉到他的视线,扬了扬册子,说:“挑不好。”
林平也不懂,窦利钧却掀开其中一页问他柜子好看吗?林平觉得木头颜色跟他屋子里的主色不协调,迟疑了下,还是摇头。
窦利钧附和道:“我也觉得。得去家具市场挑。”林平正寻思跟他道个别提着行李就走了,紧跟着听他说到:“帮我看看呢?”
林平老好人性子作祟,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不知怎麽就把看家具的活儿给揽下来了。窦利钧要去上班,没时间看,走之前居然给林平留了伙食费。林平摆手说不要,收钱算怎麽回事。窦利钧说晚上想吃肉了,问林平会不会做。
这话要搁以前,林平指定不会,家里惯的。他是跟韩元就在一起后才慢慢学着做家常菜的,韩元就很给面子,弄的林平学做菜还学出了成就感。只是后来韩元就工作忙,他俩一起吃饭的机会慢慢变少。
林平说会。
窦利钧夸他两句,说了句劳驾,人就出门去了。
林平在他走后肩膀猛地垮下去,说不上来的疲惫。如果不找点事情做,他怕他忍不住陷入思维的漩涡。他想韩元就,不可避免的,他想人怎麽能这麽干脆这麽果断。韩元就是个极其现实的人,这点林平比谁都清楚,现实点好,努力生活的人并不应该遭到谴责。
可是林平自己呢?林平靠在窦利钧那张烟灰色的软皮沙发上,扭头看到窗外枝桠错乱的树,风把枯黄的叶子吹下来,纷纷扬扬。他想起童话故事,公主和王子经历挫折后在一起。林平呼出一口气,公主不会为豆角一斤几毛钱而发愁,他终究不是活在童话故事里。
他当真去家具市场给窦利钧挑柜子去了。林平分不清木头的好坏,但隐约知道合成木板不好。得要实木。他挑挑拣拣,尽管最终一无所获,但等下次窦利钧问他的时候他可以给出意见。
很快,到了周末,窦利钧叫着林平出去看衣柜,林平每次听到窦利钧问:你喜欢这个吗?内心就会升腾出一种怪异的心理。为什麽要问他喜不喜欢?不是应该先问自己喜不喜欢吗?
窦利钧在察觉到林平的犹豫和搪塞后,便不再发问。他识趣极了。只是情绪转换的也快。林平不知道自己哪里惹他不开心,两人到商场吃饭时气氛仍有些僵。
地球是圆的。约等于人绕来绕去终究会遇见。世界怎麽那麽小,林平隔着围栏的玻璃看到韩元就和拐着他胳膊亲昵的女孩子,人登时愣住。林平太熟悉韩元就了。韩元就不喜欢在大庭广衆之下与人表现的亲近,无论男女。林平认为这跟家庭教育有关,上一代的人感情含蓄,表达委婉,从不说爱,因为爱不能当饭吃。吃了吗可以随时挂在嘴边,爱却不可以。固有的方式总叫人放不开,也叫人难为情。